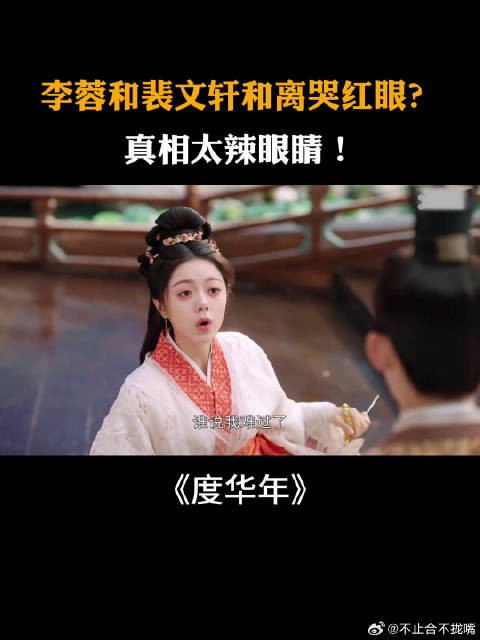作者简介
杜新豪,1987年生,山东临沂人,科学史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史与明清科技史的研究。
内容提要
Abstract
本文根据《便民纂》中的引述资料及图像判定其成书时间不早于嘉靖年间,据此纠正了前人把其误认作《便民图纂》祖本的观点,并断定《便民纂》为当时书坊雇佣文人在抄袭《便民图纂》的基础上而簒成的一本“四民通用”的日用类书,撰刻者企图通过对《便民图纂》的改造来吸引更多阶层读者的青睐,以增加其销售量,这亦是彼时其他日用类书在编纂之时所惯用的伎俩。
《便民图纂》是明代颇具代表性的一部民间日用生活指导手册,它以记载农业生产技术为主,兼及祈禳涓吉、课晴占雨、医药卫生与食品制造等各门类实用技术知识,仅在明弘治至万历中期的百余年间就至少被刊刻过六次,说明其在当时颇受欢迎。虽然四库馆臣因该书内容冗琐复杂,且不名一家,故将其列入杂家类,但因为其中囊括着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揭橥了明代农业社会的诸种新面相,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农学著作,故农史学家围绕其撰者、版本流传以及其中包含的农业新知进行过诸多探究,亦取得了丰硕之成果。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弘治壬戌版《便民图纂》抄本,与国内现存的版本略有不同,蒙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孙显斌馆长惠赠。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残破不全的明刻本《便民纂》十四卷,未题撰者,也无序跋,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便民图纂》的祖本。1959年,中华书局在影印郑振铎藏《便民图纂》万历于永清本时首次提出此观点,编辑在该书后记里写道:“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成化、弘治之间刻本的《便民纂》十四卷,不题撰者,核其内容,正是《便民图纂》的祖本”,万国鼎先生亦撰文对此表示赞同,多年后,复旦中文系陈麦青在仔细翻阅《便民纂》全书并将它与《便民图纂》进行了反复校核后,认为影印本后记中关于《便民纂》系《便民图纂》祖本的结论是确凿无疑的。其后这种观点便被学界奉为圭臬。
认定《便民纂》为《便民图纂》祖本的学者们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两书目次相似,且相互对应,只是次序稍有不同而已,为简便起见,故对两书章节对应关系列表如下(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便民纂》的绝大部分章节在《便民图纂》中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章节,他们据此认为在刊印《便民图纂》时,撰者邝璠调整了《便民纂》的类目次序,把《耕织图》添加到前面,并将其中的诗词改为竹枝词,其次把《便民纂》中大谈琴、棋、书、画等与农民日常生活无关的《辨识类》大幅删减,仅把某些对日用民生有用的条目压缩到《制造类》中。导致得出《便民纂》是《便民图纂》祖本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两书每章条目之多少与每个条目的长短,以农桑部分为例,《便民纂》比《便民图纂》多出“耙劳”、“岁宜种谷”、“播种时宜”、“播种地利”、“灌田”、“拣稗”、“除垛田稻”等诸多条目,而且即便是同一个条目,其在《便民纂》中的叙述也比在《便民图纂》显得更加冗长,如“种绿豆”条,《便民纂》曰:“宜四月,种有蓝色、绿色,又有宜摘角或宜连稿收,终是稿收者便”,而在《便民图纂》中,这条仅有“宜四月”三字,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便民图纂》是在《便民纂》基础上的进一步删减与剔除,似乎看上去《便民纂》确为《便民图纂》的祖本。
表1 《便民纂》与《便民图纂》目次之对应关系
《便民纂》目次
《便民图纂》与之相对应章节
卷一《诸占类》
卷六《杂占类》
卷二《月占类》
卷七《月占类》
卷三《月禳类》
卷八《祈禳类》
卷四《剋择类》
卷九《治吉类》
卷五《树艺类(上)农桑》
卷二《耕获类》、卷三《桑蚕类》
卷六《树艺类(中)草木花实》
卷四《树艺类(上)种诸果花木》
卷七《树艺类(下)蔬菜》
卷五《树艺类(下)种诸色蔬菜》
卷八《牧养类》
卷十三《牧养类》
卷九《法制类(上)调治饮食》
卷十四《制造类(上)》
卷十《法制类(下)造治物用》
卷十五《制造类(下)》
卷十一《辨识类》
无对应章节
卷十二《广嗣类》
卷十二《调摄类(下)》
卷十三《起居类》
卷十《起居类》
卷十四《摄生类(上)医治》
卷十一《调摄类(上)》
无对应章节
卷一《农务之图、农红之图》
笔者在翻阅《便民纂》时偶然发现两条重要材料,导致对其成书的年代产生了怀疑。目前来看,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便民纂》极可能是孤本,该书业已破损,书中并无任何关于其版本的记载或蛛丝马迹,文献检索信息上也仅注明该书为明刻本,并未有进一步详细的信息。而在前述1959年版中华书局影印《便民图纂》的后记以及万国鼎、陈麦青二位先生的文章中,却提及该书为成化、弘治间的刻本,可惜皆未给出确凿的史料依据。笔者在该书的卷五《树艺类(上)农桑》中读到“垦荒”条时意外发现一条可判断该书成书年代的史料,兹录于下:
凡开垦荒田,须烧去野草。犁过,先种芝麻一年,使草木之根败烂,后种五谷,则无荒草之害。盖芝麻之于草木,若锡之于五金,性相制也,务农者不可不知。顾东桥中丞曰:有山场荒地,须合力尽开,仍就里併开天池,蓄水备旱,且可杀下山骤水。谚云:坐贾行商,不如开荒。
该条目在论述山场开荒技术时引用顾东桥的言论,并称其为中丞。顾东桥即明代学者顾璘,璘字华玉号东桥,因而世人多称其作顾东桥,王阳明曾写信与其辩论过格物,《明史》对顾璘的生平有如是记载:
顾璘,字华玉,上元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广平知县,擢南京吏部主事,晋郎中。正德四年出为开封知府,数与镇守太监廖堂、王宏忤,逮下锦衣狱,谪泉州知州。秩满,迁台州知府。历浙江布政使,山西、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所至有声。迁吏部右侍郎,改工部。董显陵工毕,迁南京刑部尚书。罢归,年七十余卒。
通过此则材料可看出,顾璘仕途坎坷,虽先后担任过诸多职务,但直到仕任山西后才第一次担任巡抚这个官职。清人梁章钜曰:“今巡抚之称中丞,盖沿于此。明人如陈一元有《送谢寤云中丞移镇粤东》诗……至今遂沿为故实”,故而得知明清两代称巡抚为中丞,故顾璘被称为中丞只有可能是在任山西巡抚之后。既然《便民纂》的撰者称顾璘为中丞,那么其写作时间当不会早于顾璘任山西巡抚之前。根据明人文征明为顾璘所撰的《故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顾公墓志铭》来看,顾氏“庚寅召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故其履职山西的的年代当在嘉靖庚寅(1530年)之后,相应《便民纂》的写作年代也便不会早于嘉靖庚寅年。而现今发现的《便民图纂》最早刻本为弘治十五年刻本,所以《便民图纂》的成书年代至少不会晚于弘治十五年,由此可以推断弘治年间就已成书的《便民图纂》不可能脱胎于嘉靖庚寅后才成书的《便民纂》,而后者就更不可能是前者的祖本。
“祖本说”之谬误亦可从上海图书馆所藏《便民纂》的其他部分找到相关佐证,《便民纂》各卷的卷首均刻有卷数和目录,如第一卷卷首的文字是“便民纂卷一 诸占类”,第八卷的卷首刻有“便民纂卷八 牧养类”的文字,其他各卷亦如是,唯独第四卷却把“便民纂卷四 克择类”误刻为“便民图纂卷四 克择类”,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此本《便民纂》的成书晚于《便民图纂》,书商在刻印时误把此页《便民纂》的书名刻成当时已在民间流传颇广的《便民图纂》,所以说《便民纂》非但不是《便民图纂》的祖本,相反它却是抄袭《便民图纂》并以其为蓝本进行扩充而撰成的书籍,这正与清代书坊的盈利性商人以四卷本《陶朱公致富奇书》为底本,雇佣文人扩充的至十卷《增补陶朱公致富奇书广集》的情况相类似。
上海图书馆藏《便民纂》卷四书影
确定了《便民纂》与《便民图纂》成书的先后顺序后,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下支撑“祖本说”成立的理由,按照惯常理解,某部书籍后续刊刻的版本会较先前的版本有所改进,在排版上更高质量抑或在内容上更精练,为何后出版的《便民纂》却比它所模仿的《便民图纂》在质量上更加粗糙不堪,内容上更加庞杂无当,令人产生一种似乎《便民图纂》是在《便民纂》的基础上删减而成书的错误印象?这就需要结合明代日用类书的性质、成书过程及受众群体等因素来进一步解释。
至迟于春秋战国,中国就已基本构建起以士、农、工、商四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四民各执其业,士业读、农业耕、工业技巧、商业贸易,形成了一种“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各安其性,不得相干”的稳态社会结构,对于士人来说,其任务就是以求道为终极目标的读书并靠其来谋生。隋唐时,一种摘抄其他典籍中的同类知识并集结成册而出版的新式书籍“类书”开始在士人间流行,农、工、商三个阶层则被排除在读者队伍之外。宋时,四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松动,在谈到士人子弟的职业选择时,袁采认为“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但对于那些不能成为儒者的子弟们来说 ,亦不必苛责,“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与这种新观念相呼应,彼时镂板的类书中不但包含有士人所需要的闲情、器用等知识,还新添加了农、工阶层的技术知识,以供有志从事其他行业的读书人使用。《事林广记》中除了供读书人阅读的礼仪、翰墨等知识之外,还增添“耕织”与“悬壶”来讲述原本属于农民阶层的农桑、牧养类知识以及属于医者阶层的医药、解毒类知识,在金元间还出现了供士人与农民两个阶层共用的类书《士农必用》。迨至明代,随着工商业的兴隆与社会流动的频繁,四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愈发模糊,科场落败及无心举业的读书人纷纷开始寻找儒业之外的营生技术,面对门生对其提出的“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之疑问,连大儒王阳明都倾向于认为,士人若能处理好学与治生之间的关系,“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受此种流风熏染,弃儒从商者屡见不鲜。彼时更多读书人把营生的希望寄托到农业上,黄省曾在科举落地后就选择躬耕以自给,张履祥亦认为“学者以治生为急”,且“治生以稼穑为先”,遂雇人来经营农业,他在读书课馆之余,“凡田家纤悉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之理”。除士人外,由于当时启蒙教育成本的降低,出于记账、书信往来等方面的实际生活需要,越来越多的农、工、商阶层的子弟也入私塾或通过学习日用杂字等来读书识字,整个社会的识字率较前代有很大进步,根据罗有枝(Evelyn Rawski)的统计,在清代中国甚至有30%-45%的男性懂得读写(Knew how to read and write),这些识字的人们亦皆在营生并频繁地调换着职业,如徐光启的父亲识字并能阅读医学、星象、占候类的书籍,“尝业贾,不肯屑瑟计会,复谢去,间课农学圃自给”。对于明代这种士人寻他业谋生,民间人士也频繁换职业的状况,有学者提出“四民兼业”的概念来形容彼时这种频繁的兼业现象。这些识字者在兼业过程中体会到孔夫子那种“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技术缺乏之状况,为了迅速适应新职业并获取利润,这些兼业者迫切需要技术指导。而明代拥有着极其发达的印刷出版业,以市场销售作为盈利目标的商业性书坊、书肆大量涌现,书贾们抓住这些识字的兼业者对日用技术需求的商机,大量刊刻、兜售兼业所需要的技术手册,很快众多号称可供士农工商四阶层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指南性书籍开始出现并迅速充斥于市坊间,这些书的名字中常含有“四民便用”、“四民便览”、“士民万用”、“四民利用”、“四民捷用”等字眼,封面的图像也在暗示读者它们对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人来说皆适合阅读(见下图),试图来获取更多的阅读公众群和赚取更丰厚的出版利润。如在《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序言中其补订者武维子就大力吹嘘此书对士农工商各阶层人获取知识的功用:
士以之仕,可大受亦可小知。农以之耕,知天时亦知地利。工之所以奏技,贾之所以市倚,凡百家众技之流,其所以取捷目前者,一卷阅而了然心目,则其大用之不穷。
经过书商与文人的大力推介,这些日用类书在市场上甚是走俏,甚至在某些书肆中能力压《金瓶梅》、《西游记》等畅销小说而拔得销售头筹,其畅销性导致市场上有大量抄袭、盗版之事发生,以至于很多日用类书的封面上都刻印着对盗版者的强烈谴责及告知读者辨别其书真伪之方法。
《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便用学海群玉》封面,上面的图画暗示士农工商各阶层都可以从此书中获得他们需要的知识。
《便民图纂》为吴县县令邝璠在治时所撰,其目的是为了给治下的农民提供农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日用知识,以此来劝课农桑,该书“自树艺、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调摄之节,刍牧之宜,微琐制造之事,捆摭该备”,是一本极好的日用类书的模板。但由地方官所纂的劝农性文献的性质决定它更多关注农业与民间中下层群众所需的日用技术,且该书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所述农事多为太湖区域的农事经验,与当时天下四民通用的畅销读物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为了将其改成四民通用的畅销书籍,书坊主及其雇佣的文人墨客将《便民图纂》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他们的第一步就是将该书里涉及太湖流域区域性的农事知识转变成南北通用的知识,太湖地区的作物系统是以水稻为主,所以《便民图纂》里的农业知识注重是水稻栽培、收藏等技术,书商们在编纂《便民纂》之时增加了某些北方的知识,比如加入“耙劳”来讲述秋耕后耙劳的重要性,插入磨小麦来制作面粉的技术,增加对黍、粟、粱等北方旱地作物及其种植技术的介绍;还增补了某些南北通用的知识,如播种地利、播种时宜,灌田等,把《便民图纂》里某些具有强烈南方地域性的词条进行增补,如“藏米”条目被修改成“藏米谷”;此外,他们还仿照当时市肆上流行的日用类书的体例,将涉及农业技术的章节题目从“耕获类”改成“农桑”,以与当时日用类书的“农桑门”相呼应。第二步是向《便民纂》中增添四民中其他阶层所需要的知识,士人是阅读文本的最重要群体,当然也是购买书籍的主力,士人们的喜恶决定着日用类书的市场占有量及销量,彼时其他日用类书均把士人阶级需要的琴棋书画、翰墨音律、礼仪社交等知识列为首要内容,《便民纂》的撰者们也在《便民图纂》的基础上大量增添士人感兴趣的辨琴、辨兰亭诸帖、辨画、辨玉器、辨水晶、辨玛瑙、辨珊瑚、辨象牙等高雅知识,同时,《便民纂》还增加了从事立契、会客等商业活动吉凶日占卜的知识,以同时吸引有阅读能力的商人读者之兴趣。为了拼凑出更多的章节以彰显其书无所不包,《便民纂》将《便民图纂》的每个条目都进行了扩充,在其后引经据典,大段抄袭某些早期典籍与之相关的内容,在《便民图纂》描述农作物种植方法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对其性状、来源、食用方法与功效之考证。由于日用类书的读者以士人为主,士人无需借助于视觉图画材料即可阅读,所以《便民纂》的撰者删除了《便民图纂》中用来给粗识文字的农民看的农务、女红图,此举亦进一步节约了刊刻成本,能以低廉的价格优势获得更多的销量。
伴随着盗版、翻刻之风的盛行,明代很多日用类书都存在目次混乱且错讹颇多的缺点,与当时其他坊刻日用类书相类似,《便民纂》也存在着这些不足,如虽然书中的条目与题名都用阴影来标注,以与正文中的文字相区别,但卷二“月占类”中的正月、五月两条却没有阴影;且该书的章节颇为杂乱,如撰者莫名把农业类的“治水涸”条放在专讲调治饮食的卷九中。明代日用类书的编纂者大多为落魄的落地士人,为书坊所雇佣,即使少数日用类书标榜其作者为有名之士也多属伪托,这些作者大多籍籍无名,所撰的日用类书也基本不题撰者,《便民纂》也无撰者及序跋讯息。综合以上观点,可以断定《便民纂》即是某个书肆或书坊的书商及其雇佣的文人以《便民图纂》为蓝本所编辑的面向当时世俗市场的盈利性书籍,是劝农文献《便民图纂》在当时书商坚信天下四民皆读者的出版信念下出版的产物。
信息来源
原载《古今农业》2016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诚挚欢迎专家学者赐稿
本期编辑
饮冰(耿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