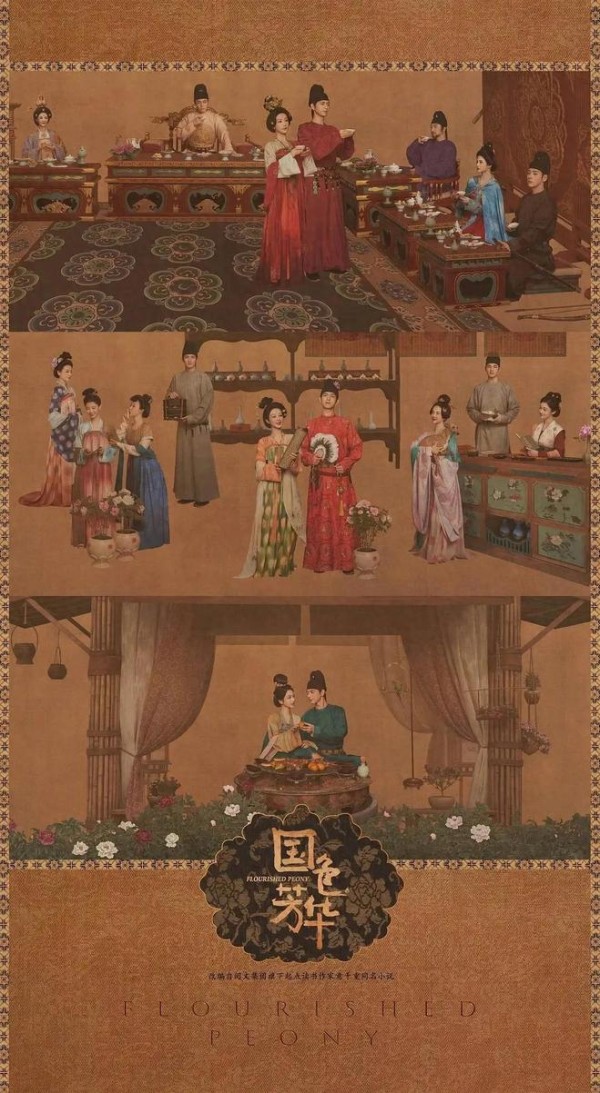悦·读
宋代渐普及的宠物饲养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丰富的重要表现,同时,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也对宠物饲养有着回应和适应。以宋代驯猫史为切入点可观察到: 猫已被各阶层普遍饲养在家,发挥着从捕鼠到相伴生活等作用,猫的宠物化进程在推进和加深,捕鼠的工具性职能在淡化和抽离,出现覆盖各阶层的典型的宠物饲养特征;带有传统色彩的“乞猫”“聘猫”在延续和发展,猫的交易大量出现,形成了与猫相关的各类市场,市场中亦有为宠物猫提供的专门服务。家猫的宠物化与宋代商品经济相结合,表现出较高的宠物化程度。
本篇文章约6387字
阅读大约需要16分钟
宋代驯猫史:宠物饲养与商品经济的交融
黎良基
猫是当今人类的主流宠物之一,学界有关中国驯猫史的研究成果已有了一定积累,其中不少学者判断宋代是中国驯猫史的关键时期。但总体看来,目前研究尚缺少宋代家猫宠物化的专门的系统论证。由是,本文以宋代驯猫史为切入点,以家猫饲养与宋代社会经济为视角,系统研讨宋代家猫的宠物化问题。
古人若认为某种动物有着特别的意义或地位,常通过“祀”来体现。祭祀猫源流久远,早在先秦就有天子大蜡八之祭,《礼记·郊特牲》记载“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也”。由此可看出: 早在先秦时就有对猫的祭祀,谓迎猫;其次,祭祀猫是因其有功于田稼,“猫”这个名称也同田稼有关,宋人释猫时以为“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另外应当明确,早期猫的形象与后世有很大不同,《诗经》言“有熊有罴,有猫有虎”,猫作为一种猛兽与熊、罴、虎并列。到宋朝时,迎猫的传统仍然被很好地延续着,蜡祭有诗云“祭列坊庸,礼迨猫虎。有功斯民,祀乃其所”,地方寺庙的壁文提到“猫虎之属莫不有祀,大抵皆民事也”,宋人“猫有功禾稼则迎,虎有功禾稼则迎,此人情忠厚之至”。
古人迎猫而祀,这种出于田稼之功的情感本是与虎同享,但猫与虎,终有着较大差异,一者走进室内被人爱而近之,一者咆哮山岭使人畏而远之。及至宋时,世人对猫的喜爱之情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与普遍,家猫宠物化也出现了明确的痕迹。
一、 裹盐迎得小狸奴——宋代养猫的盛行
猫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宋代文人的记叙中。诗云“猫跳触鼎翻”,有人“尝烧金鼎,宫猫相戏触翻。因举前诗曰:‘词人作诗,信无虚语。’”此外,《挥麈后録》言宋孝宗被选为皇储与宫猫忽然出现有关。以上现象的基础正是宫中常畜猫。事实上,饲养猫已不止限于宫中。丞相吴育能借猫眼辨认时辰,修习炼金术者刚要点火有“一大猫据炉而溺”,禅修僧人会“传来铁钵盛猫饭”,士人读书时常见“乱叶打窗猫上案”,赵蕃在给亲友写信时更提到“宁无捕黄口,亦有聘狸奴”,聘猫养猫已不限阶层。
高士自有雅兴,市井小民与猫的日常接触同样普遍。有人吟咏:“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尔,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在文士看来“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是高雅缥缈、求诸心性的佳句,而世俗之人结合自身日常生活经验套说了一个最常见的情形: 更象是猫丢了找猫。衆人“皆以为笑”,既是被此事的娱乐精神所感染,也是对“说者”所言乃家常琐事而一语破题的认同,其间机妙是民间饲猫之普遍。
宋人普遍畜猫,田舍常畜马、猫、鸡、犬,家中猫狗走失亦成为民间理讼的重要部分,家猫的境况也一定程度映照着百姓民生。金州有庙名望仙观,时人认为观中天尊理讼尤其灵验,多求天尊理讼解难,“其邑中失走猫犬、巨细论讼,陈状于殿壁之上,动盈百幅矣。至今常然”。诸多走失猫狗类事求神灵理讼,反映出当地饲养猫狗风气颇盛,主人也对猫狗较为珍惜,急欲寻回。战乱灾荒时,宋代史家曾把猫的境遇作为城市衰败的表现之一。靖康城破日,《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将其惨状表述为城内“疫死者几半。物价踊贵……城中猫犬残尽,游手冻馁死者十五六,遗胔所在枕籍”,城陷两月之后,丁特起嗟叹“小民樵苏不给,饥死道路者以千计。市井所食,至于取猫鼠,甚者杂以人肉”。城池遭遇兵燹,城中饲养的无数猫犬被殃及,乱离中家猫的遭遇已同城中百姓的命运相互映照。
二、 人间有俊物——家猫的宠物化之路
(一) 捕鼠
正如迎猫是因其食田鼠,宋代大部分人养猫的最初动机是利用它的捕鼠特性。虽同是捕鼠,这时的猫已经同前代有了区别,它们更多地从田间走向居室,文士们对猫的称赞也主要从保护田稼变为看家卫厨、护持经卷。
1.居家捕鼠
猫在居家生活中辛勤捕鼠、居功至伟的形象在宋人诗文中存留丰富。黄庭坚以西汉名将周亚夫作比,言猫是“将军细柳有家风”并“一箪未厌鱼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不计奖酬又屡立奇功。陆游给猫起名“粉鼻”,夸它“连夕狸奴磔鼠频,怒髯噀血护残囷”,写诗盛赞其“鼠穴功方列,鱼飱赏岂无。仍当立名字,唤作小于菟”,既用鱼餐犒赏,又将虎的别名赠予家猫。宋人希望家猫捕鼠能威猛似虎,张耒曾为一幅虎图赋诗:“烦君卫吾寝,起此蓬荜陋。坐令盗肉鼠,不敢窥白昼”,虽有画虎似猫的嘲弄,确也侧面表现出家猫居家捕鼠的功能。
宋代咏猫诗广受欢迎,论流传闾里要数黄庭坚的《乞猫》,其文曰:“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将鼠扰居所,唯乞一猫方能平息的情形描绘得生动清新。宋代诗论载,该诗“虽滑而可喜。千载而下,读者如新”,明白体现出咏猫诗的流行和时人对猫的喜爱。
2. 护持经卷
一般人家养猫是为了卫寝护囷,而文士家中通常满藏经卷,往往担忧鼠患猖獗,“嚼啮侵寻到简编”,于是“生计惟黄卷”的“腐儒”只好“乞取衔蝉与护持”。家猫捕鼠护持经卷的功劳,为士大夫喜爱赞赏且津津乐道,其对猫的感情也在这种价值欣赏中逐渐升温。“狸奴当努力,鼠辈勤诛锄”“屋头但怪鼠迹絶,不知下有飞将军”,从勉励到夸赞再到欣赏,类似诗文在宋人笔记文集里频频出现。陆游案上书遭鼠害,産生“向能畜一猫”的强烈需求,需求引导行动,陆游“裹盐迎得”一只猫,不负期待发挥了“尽护山房万卷书”的显著贡献。功勋在此,陆游为无法给它舒适生活而觉惭愧,感叹家中条件有限,让猫“寒无毡坐食无鱼”,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狸奴护简编”让陆游越发欣赏,赞道“人间有俊物,求买敢论钱”。
价值欣赏催生情感,梅尧臣言“自有五白猫,鼠不侵我书”,同样记下了家猫护持经卷之功,而他在猫死后“祭与饭与鱼”,用怀念亲人故友式的行为表达思念,已不只把家猫当作捕鼠工具,而是对其産生了更亲近的情愫。
(二) 相伴生活
清人黄汉将养猫的好处归纳为“四胜”,除了捕鼠护衣书、不用太多照顾、喂养简单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冬床暖足,宜于老人”。宋人讲“猫暖眠毡褥”“顾有狸奴同席温”,意在年老体衰、孤寂清寒之时,幸好有狸奴相伴,共度长夜,暖足御寒,人与猫“高眠永日长相对,更约冬衾共足温”,显露的是朝夕相伴又亲密无间。
猫既能护衣护粮护书,又能在寒夜共寝,御寒暖足,使得猫与主人的感情逐渐升温,关系越发亲密,平常闲时“睡猫随我懒”,俨然成为生活伴侣。吕本中将家猫取名为“师奴”,师奴“竹舆游历遍诸方。火边每与人争席,睡起偏嫌犬近床”,随他游历、伴他生活。不仅如此,猫还“受戒不捕鼠,听经如欲应”,仿佛有了灵性,“能与儿童较几许”。潦倒愁苦、困顿寡居时,有“狸奴伴寂寥”,与主人“娱晨暮”“共茵席”“争席隈”,这时家猫是可贵的陪伴者、情感寄托对象。
三、 日饱鱼餐睡锦茵——宠物化后的猫
(一) 纯粹情感寄托——家猫核心功能的变化
猫既可发挥实用功效,又俨然成为生活伴侣,让人越发爱怜。在猫成为生活伴侣,宠物化愈渐推进的过程中,生活的舒适、主人的疼爱也使其渐渐失去了一些工具性作用,最初为人所求所“祀”的捕鼠“天性”便趋于隐退消失。富贵人家的猫“日饱鱼飱睡锦茵”,享受着优厚待遇,同寻常百姓养猫捕鼠似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家猫不捕鼠却仍不减主人爱护,这样的趋势已经走向民间,猫的宠物化更为普遍。
家猫不再用心捕鼠,从驯猫史视角看,实质是适应了宠物化的饲养方式。以前斗鼠的刚猛一去不返,自得于“惰得暖而安,饥得饱而驯”般舒适安逸的宠物生活,饲养者对这种“聪明”的性情也由恼怒转向无可奈何。家猫不再捕鼠成了一种常态,“看君终日常安卧,何事纷纷去又回?”主人渐少了抱怨而更关心宠物猫的日常行踪,不再捕鼠最终并未影响家猫与主人的感情。“狸奴不执鼠,同我爱青毡”,两者依然相伴生活,亲密无间。
爱猫情节在宋人文集中常有体现。胡仲弓家“瓶中斗粟鼠窃尽,床上狸奴睡不知。无奈家人犹爱护,买鱼和饭养如儿”。胡家猫对鼠害猖狂已然充耳不闻,虽然胡仲弓有些许无奈,但家人对猫却爱护倍至,似亲子般照顾,家猫饲养已经表现出典型的宠物化特征。如此状况下,猫对鼠的威慑力也有所下降。“痴儿效猫鸣,此计诚已拙”正是对世情变幻的调侃,许多人家畜猫已渐脱离其最初用来捕鼠的工具性目的,家猫的主要职能已存在被“生活伴侣”取代的趋势。
上述诗文虽体现家猫的宠物化趋势,但仍不自觉将养猫同捕鼠相联系。宋人张至龙曾以为“犬眠苍玉地,猫卧香绮丛”确是可喜可爱,但“倘无鼠与盗,猫犬命亦穷”,捕鼠依然是家猫存在的立足之本。然而,宋代家猫的宠物化已经出现突破性发展,呈现纯粹的情感寄托,家猫的宠物特征愈发成为独立价值。
不同上述,宋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述突破了养猫捕鼠的固定搭配而专论主人对猫的“特见贵爱”。张邦基对猫的华美可爱赞不絶口,言其“衔蝉毛色白胜酥,搦絮堆绵亦不如”,以至于自己减口也要让猫“从今休叹食无鱼”。一名官员的母亲高氏养了只大猫,宠爱非常,几乎片刻不离,“猫娇呼,则取鱼肉和饭以饲”,高氏偶得“饥疾”,状况严重到“每作时,如虫啮心”,却“取鹿脯自嚼而啖猫”。张邦基和高氏的饲养已体现出强烈的宠物情结。
受到特别的悉心照料是家猫宠物化后的重要表现。主人早晨起来首先“欲营猫饭”,突降大雨担心的是“饥猫避谁屋,竟夜不能归”,家猫繁育幼崽主人兴奋欣喜,感觉“卧看跳嬉亦一奇”。建康有“鬻酰者”养有一猫,“甚俊健,爱之甚”,因为猫长得漂亮尤其喜爱,后来猫不幸死亡,“不忍弃”,仍然念念不舍地把猫放在自己身边“数日”,直到有些腐坏发臭才“不得已,携弃秦淮中”,奇异的是鬻酰者竟然觉得猫好像活了过来,“下救之,遂溺死”,为了自己养的猫,死不肯离,舍命相救,主宠情深不言自明。又有桐江民,对猫“爱之甚,坐卧自随,但日观其食饥饱,暮夜必藉而寝,或持置怀抱间,摩手拊惜,出则戒婢谨视之”。桐江民自随其猫,可谓极致爱怜、视同珍宝,是宋人把“猫”极端宠物化的例子。宋代皇宫中对猫的喜爱亦打破了帝王禁忌。“神宗生戊子年,当年未闻禁畜猫”,宋神宗赵顼本命为鼠,按五行相克文化本应避开天敌,如果猫没有较为深刻的宠物化趋向而只是作为捕鼠工具使用,打破这样的禁忌并非易事。
(二) 宋代画作与墓葬中家猫的宠物化表现
正如上文所见,宠物化过程中,家猫渐渐淡化了捕鼠能力,把猫当作宠物来看待的主人亦将关注点放在了猫的观赏、陪伴和玩乐上,这在艺术作品中有更直观的反映。宋代绘画作品中,猫的形象往往以观赏和玩乐为主,多体现宠物情趣而少见捕鼠姿态。以北宋官方编修的《宣和画谱》为例,五代李霭之“尤喜画猫”,徽宗御府共藏其所画十八品,均为画猫,其作品有:“药苖戏猫图一,醉猫图三,药苖雏猫图一,子母戏猫图三,戏猫图六,小猫图一,子母猫图一,虿猫图一,猫图一”;王凝“工为鹦鹉及狮猫等。非山林草野之所能,不唯责形象之似,亦兼取其富贵态度”,御府藏有一“绣塾狮猫图”;何尊师“尤以画猫专门,为时所称”,御府共藏其作三十四品,其中三十三品皆为猫画,有:“葵石戏猫图六,山石戏猫图一,葵花戏猫图二,葵石群猫图二,子母戏猫图一,苋菜戏猫图一,子母猫图一,薄荷醉猫图一,群猫图一,戏猫图五,猫图一,醉猫图十,石竹花戏猫图一”。金人元好问曾得见何尊师所画醉猫图,其间“牡丹花下日斜初”,景致美不胜收;猫“饮罢鸡酥乐有余”,其神态“侧辊横眠却自如”,可谓闲适至极。总之,统计《宣和画谱》所记録的猫画,以观赏和玩乐为主题的占絶大多数。除官方所收名画外,民间画作亦有同样趋势。刘克庄曾见杨朴所画《移居图》,其中“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儿”;宋代豫章画扇上有“牡丹三株黄白相间盛开,一猫将二子戏其旁”,杨万里为其题诗:“暄风暖景政春迟,开尽好花人未知。输与狸奴得春色,牡丹香里弄双儿。”
猫宠物化后主供观赏玩乐而不再捕鼠,引起部分人的不满,故这一现象也被用于讽刺时政,如“道士李胜之画捕蝶狮猫,以讥当世”,又如苏轼言“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然而,跨过不满与讥讽的理念争端,出于爱怜而以“戏”为题的猫画,已然成为时代欣赏与追逐的风尚。考古发现的宋代墓葬里,正可以捕捉到这样的风尚。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着市民文化兴起,墓葬世俗化特征明显,墓葬中的壁画与陪葬物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反映,也是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构建。猫作为代表安逸生活的意象,出现在了宋代墓葬壁画里。宋墓壁画中绘有猫的图像装饰“有着较为固定的搭配模式,通常与侍女、直棂窗和其他一些日常家居用品搭配出现”,是生活场景中的一个元素,而位于侍者之列亦有侍奉主人之意。画中猫“以蹲坐者居多,颈部均系有丝线或铃铛”,呈闲适之态,当是观赏玩乐之用。此类风格的壁画,表现出墓主不仅生前爱猫,在死后世界也想要其陪伴。在河南新乡公村宋代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在棺床南部靠近墓主人骨架处清理出了一批动物骨骼。经过专门研究,这批动物骨骼被认定属于同一家猫个体,“呈现一定程度的豢养杂食性特征”,系“特意安置在墓主身旁”,起着在死后世界陪伴墓主的作用。
四、 为问衔蝉聘得无——家猫与宋代社会经济
宋代家庭养猫的盛行扩大了对猫的需求,也催生了与猫相关的市场。获取猫的一大途径是求取于近邻和亲友,谓之“乞猫”。清人黄汉引《丁兰石尺牍》言“古人乞猫,必用聘”。以聘乞猫,主要是用鱼或盐去交换,所谓“贯鱼乞狸奴”“裹盐迎得小狸奴”,“聘”固然有着礼节和习俗的意思,鱼可做猫食亦自不必说,对于“裹盐”,古人以为“聘猫用盐,盖亦取‘有缘’之意”。乞猫的“聘礼”并不限于鱼与盐,有用笋即“以笋乞猫”,更有“青蒻裹盐仍裹茗”“更令女手缀红繻”,这里除了盐外还有使用茶和纺织品,有着以物易物的味道,这不单是人际交往的一部分,也应存在着实际收益。正因如此,乞猫之人需费心聘猫,养猫之家也会特意繁育,讲究养母猫为佳,等到“他时遂生育,邻里转相予”,同今日的家庭猫舍已大致相似。可见,聘猫既带有礼尚往来的传统色彩,同时也存有交易买卖的因素。
除以实物为聘之外,还有直接以钱交易的例子。宋人讲“狸花最直钱”,“譬之人家,市猫于邻”,描绘猫的获取时使用“市”“购”等语;又有猫走失“购求竟不获”,后来发现是被人偷捉到店,店内“其物则市之猫犬类也”。价值上,猫因品种不同价值差异较大,唐时便有“张搏好猫,其一曰东守、二曰白凤、三曰紫英、四曰袪愤、五曰锦带、六曰云图、七曰万贯,皆价值数金,次者不可胜数”。及宋时,《夷坚志》中载孙三与其妻将白猫染红,设计了一出以猫为核心的诈骗伎俩,并最终哄得宫中内侍高价收购,“以钱三百千取之”。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猫的交易还有了“契约”,如《类编历法通书大全》收録“猫儿契式”,其内容如下:
一只猫儿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长养,护持经卷在民间。行契〇〇是某甲,卖与邻居某人养。三面断价钱〇〇〇〇随契已交还,买主愿如石崇福,寿如彭祖禄向迁,仓禾自此巡无怠,鼠贼从兹捕不闲,不害头牲并六畜,不得偷盗食诸般。日夜在家看守物,莫走东边与西边,如有故违走外去,堂前引过受笞鞭。年月日,行契人。
这纸纳猫“契书式”明言“卖”“买主”“三面断价钱”,可见猫的买卖确实存在,而且已经比较规范。当然,“猫儿契式”与一般契约有较大区别,还表达一种吉祥、祝福之意,可能也是宗教仪式渗透民俗的表现形式。
以猫为物件的普遍交易还可从宋人对産猫地的叙述里窥见。时人“谓海州猫为天下第一”,亦言“今海州猫最佳,俗云海州猫曹州狗”。猫的宠物化,也可在宋人对産猫地的描述中表现出来,《嘉泰吴兴志》与《咸淳临安志》记载了其地专有不以捕鼠为务的“宠物猫”,《嘉泰吴兴志》载“猫,又家畜以捕鼠,近有黄斑者,有毛长如獶者,虽似可爱但不能捕鼠,实无用也”,《咸淳临安志》则更清晰地把握住了宠物猫的特性,谓“都人蓄猫,有长毛白色者名曰狮猫,盖不捕之猫,徒以观美特见贵爱”。
宋人既有市猫需求,相应也便渐催生出了“猫市”。北宋时,相国寺作为贸易繁荣的首都中心市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其中有专门的动物售卖区,“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在这动物市场中,猫便是主要交易品类之一。猫的品类也有增多,“虎斑,旧时罕有,如今亦不足贵”。除却交易市场,都城有针对买猫和养猫者的特别服务,城中居民住户如若养猫,会有商家每日“供鱼鰌”“供猫食并小鱼”,这些特别服务推动了宠物猫饲养食品的专门化,“纤鳞喂乳猫”已经成为养猫人士的讲究与潮流。南宋的猫市更存在进一步的发展,临安“猫市”其经营项目有“猫窝、猫鱼、卖猫儿、改猫犬”,包含着针对宠物猫“吃、穿、住”甚至养护等方面的专门服务,宋代猫市的繁荣和宋人饲养宠物猫的盛况已可见一斑。
结 语
个人之于世界同太仓稊米,饲养宠物便是社会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选择克服孤寂感的方式。从驯宠史看,唐、五代有一些零星的记载表明猫已存在被作为宠物豢养的趋势,而宋代正是猫在中国宠物化的关键时期。考古证据显示新乡宋墓出土了我国迄今可确定的第一只宠物猫。分析宋代文献亦可见,无论王室权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在家中普遍养猫并时常将其作为宠物。宋人与猫的互动关系是多样的,既有承袭农业传统的祭祀,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捕鼠、护粮卫书、暖足御寒、相伴相随,可以观察到一些家猫核心功能已发生变化——成为主人纯粹的情感寄托。在这种互动中家猫的宠物化程度日益加深,伴随着这种宠物化,催生出了相关联的交易与服务,宋代社会生活在这里呈现了一个较为具体和微观的侧面。
原文载《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引用时请注明出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