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清华积极心理学十六讲》
市场资讯 07.27 07: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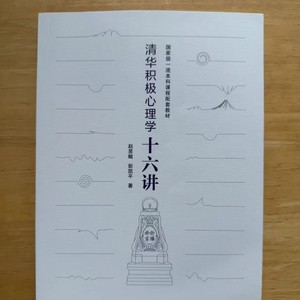
(来源:海运经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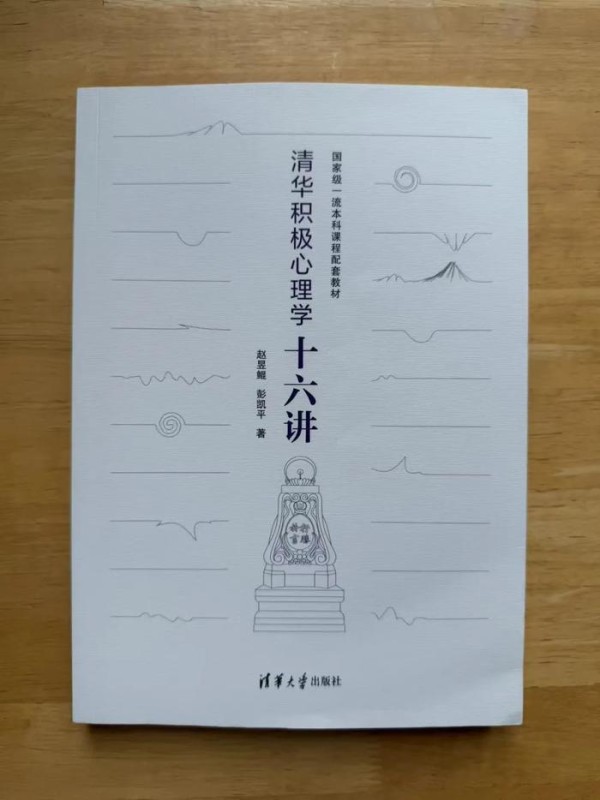
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兴起的心理学研究分支,它打破了传统心理学聚焦心理疾病、缺陷和痛苦的研究范式,转而关注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优势潜能与幸福体验,旨在探索“如何让生活更有意义”“如何培育人的 flourishing(蓬勃发展)”。其核心主张是:心理学不仅要“修复损坏的东西”,更要“培育美好的东西”,最终帮助个体与社会实现良性发展。
一、起源与发展:从“问题导向”到“优势导向”
积极心理学的正式诞生以1998年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并提出“积极心理学”倡议为标志,但这一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更早的哲学与心理学传统。
1. 思想渊源
哲学层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eudaimonia(幸福/ flourishing)”概念、斯多葛学派的“美德实践”思想,以及现代存在主义对“自我实现”的探索,为积极心理学提供了理论根基。
心理学层面:人本主义心理学(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疗法”)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潜能,为积极心理学奠定了实践基础;但积极心理学更注重通过科学实证方法研究积极心理现象,而非单纯的理论思辨。
2. 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心理学长期以“治疗心理疾病”为核心任务(如精神分析关注潜意识冲突、行为主义聚焦异常行为矫正),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减少痛苦不等于获得幸福,健康的心理状态不仅是“没有疾病”,更应包括积极的情绪、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感。积极心理学正是在这一需求下应运而生,填补了传统心理学对“积极面”研究的空白。
二、核心研究领域:积极体验、积极人格与积极社会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 积极情绪与体验
这一领域聚焦个体的积极情感状态及其对心理功能的影响,核心理论包括:
“拓展-构建理论”(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积极情绪(如喜悦、感激、敬畏)能拓展人的认知与行动范围(如喜悦让人更愿意探索新事物),并长期构建个人资源(如人际关系、创造力、心理韧性)。例如,常体验“感激”的人更易建立互助关系,增强应对压力的能力。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由塞利格曼等人提出,指个体对生活的整体满意感,包括“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对生活领域(如工作、家庭)的满意”等维度。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不仅是一种感受,更能预测健康水平与寿命长短。
心流(Flow):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指人在全情投入某项活动时(如创作、运动),因技能与挑战匹配而进入的“忘我的愉悦状态”。心流体验能提升自我效能感,并成为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2. 积极人格特质与优势
积极心理学反对将人简化为“问题的集合”,转而关注个体稳定的积极特质,核心研究包括:
性格优势与美德(VIA分类体系):塞利格曼与彼得森通过跨文化研究,总结出人类共通的6大美德(如智慧、勇气、仁慈)及24项性格优势(如创造力、正直、感恩),并认为“发挥优势”是实现幸福的关键。例如,擅长“好奇心”的人更易在探索中获得意义感,而“团队合作”优势强的人更易在人际关系中感到满足。
心理韧性(Resilience):指个体在逆境中恢复与成长的能力。研究表明,韧性并非天生,可通过培养乐观心态、建立社会支持系统等方式提升。例如,将挫折解释为“暂时的、可控的”(而非“永久的、不可改变的”),能增强人面对困境的适应力。
3. 积极社会环境
个体的积极发展离不开支持性的社会系统,这一领域关注:
积极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如婚姻、友谊)是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其中“感恩表达”“共情倾听”等互动方式能增强关系质量。
积极的组织与社区:如“积极教育”(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优势与幸福感)、“积极组织”(企业通过赋予员工自主权、意义感提升工作投入),以及“积极社区”(通过公共空间设计、互助活动促进居民联结)。
三、实践应用:从理论到生活
积极心理学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探索,更在于其可操作的实践方法,常见应用包括:
积极干预技术:如“三件好事练习”(每天记录三件值得感恩的事,提升积极情绪)、“优势发挥计划”(有意识地在生活中运用自身优势)、“认知重构”(用积极视角重新解读事件)等,已被证实能有效提升幸福感。
在教育中的应用:通过“成长型思维”培养(鼓励学生相信能力可通过努力提升)、“心流课堂设计”(让学习任务与学生能力匹配),帮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
在临床中的应用:与传统心理治疗结合,通过强化来访者的优势(而非仅关注症状),提升治疗效果。例如,对抑郁症患者,除缓解抑郁情绪外,引导其发现自身的“坚持”“友善”等优势,增强康复动力。
四、争议与反思
积极心理学并非完美无缺,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批评:
部分学者认为,它过度强调“积极”,可能忽视真实的痛苦与社会结构性问题(如贫困、歧视),陷入“盲目乐观”的误区。
对“幸福感”的量化研究(如用量表测量主观幸福感)可能简化了人类体验的复杂性,难以涵盖不同文化对“幸福”的多元理解。
对此,现代积极心理学逐渐走向整合:既承认痛苦存在的必然性,也强调在接纳痛苦的基础上培育积极力量;同时,更注重结合文化背景(如东方文化中的“和谐”“中庸”对幸福感的影响),使理论更具普适性。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是“回归心理学的初心”——不仅关注“人为何会痛苦”,更探索“人如何能更好”。它提醒我们: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在发挥优势、联结他人、投入意义感活动中逐渐构建的过程。正如塞利格曼所言,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让普通人的生活更丰盈、更有活力”,这一使命使其成为当代心理学中极具生命力的分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