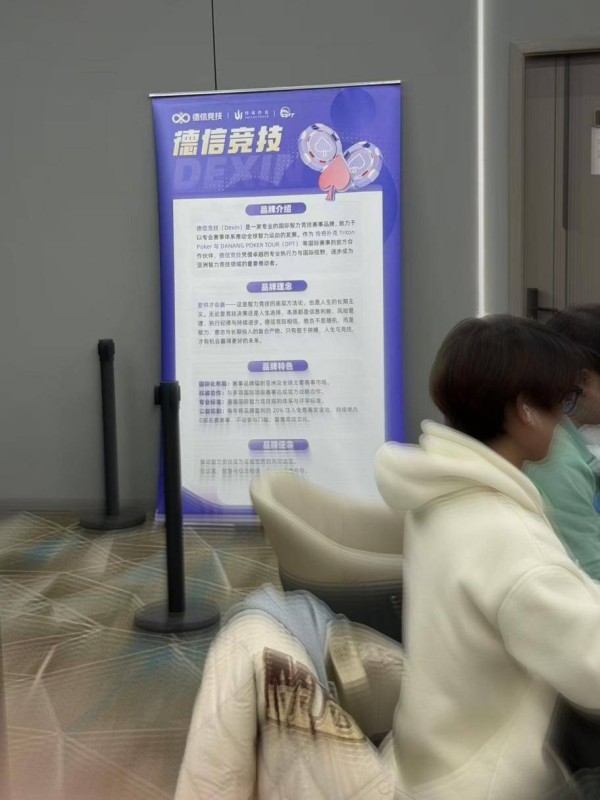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陈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玩劳动”是数字时代“产消合一”劳动行为的典型具象表达。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玩劳动”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生产方式作用下的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在劳动与休闲统一的过程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劳动,释放劳动创新的潜能,是“玩劳动”在数字时代的积极朝向。然而,“玩劳动”往往与享乐主义、“躺平”主义、消费主义等相互交织,以享乐化、娱乐化、否定化的形式出现,对社会劳动观的形成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根本,发挥劳动精神引领作用,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中引导和规约“玩劳动”,赋予其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行动标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玩劳动 价值引导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经济社会出现了以数据产品生产和掌握信息为核心的数字化生产范式,且催生了全新类型的“产消合一”劳动形态。“玩劳动”作为“产消合一”劳动行为的典型具象表达,对传统劳动实践和劳动观形成了解构和反构。与此同时,“玩劳动”与享乐主义、“躺平”主义、消费主义等社会思潮相互交织,以享乐化、娱乐化、否定化的形式出现,对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正确劳动观的形成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审视“玩劳动”的生成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和规约“玩劳动”,并赋予其明确价值导向和行动标准,对引导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玩劳动”概念的产生、发展与厘清
“玩劳动”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达拉斯·斯麦兹(DallasSmythe)提出的“受众商品”理论。斯麦兹认为,观众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被强制要求观看商业广告,这相当于被迫承担了一种接收营销信息的无偿劳动,并将其称为“受众劳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平台用户的活动越发受到学界的关注。蒂兹纳·泰拉诺瓦提出了“免费劳动”的概念,他强调,数字媒介用户为了获取数字平台免费的在线服务而承担了生产性的工作,无偿为平台企业创造经济收益。受泰拉诺瓦“免费劳动”概念的启发,库克里奇提出“玩劳动”的概念来描述数字游戏产业中游戏模组爱好者自发免费为游戏平台修改和创作游戏内容的无偿劳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学界普遍讨论的“玩劳动”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在娱乐过程中附加创造的数据信息产品,如用户在PC客户端和移动客户端进行网络购物、浏览网页、点赞、评论、休闲出行等活动而产生的大量数据;二是个体在娱乐过程中创造的数据信息产品,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创作的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等在内的数据产品以及游戏产业中数字游戏产品的生产等。其中,“玩劳动”与传统劳动范畴最鲜明的区别是生产性与消费性的统一,即“产消性”,这也引发了学界的激烈讨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掀起了讨论的开端。福克斯认为,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的概念需要扩展,以包括正常工资关系之外被剥削的人。例如,互联网用户生成内容,即“玩劳动”的劳动成果被资本无偿占有和剥夺,用于资本的积累。针对福克斯的观点,亚当·阿维德森和伊拉诺·科洛尼亚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互联网用户的价值创造过程以及社交平台企业的价值实现过程实际上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框架,将互联网用户价值创造理解为基于启动和维持情感关系网络的能力,以及基于声誉的金融经济相关的价值实现。对此,福克斯提出“互联网产消者商品理论”进行回应。福克斯认为,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互联网用户在平台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个人资料数据、用户生成的内容和交易数据”等数据信息被商品化,成为数据商品。因此,互联网用户“既是数据商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数据商品的生产者”,作为生产者,“用户从事的是永久性的创意活动、传播、社区建设和内容生产”,而这种生产性活动为社交媒体提供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用户在平台中的消费活动同时也是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此后,众多学者纷纷参与这场探讨中。
对此,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有的学者在分析“玩劳动”的生产性及其理论逻辑时,指出“玩”与“劳动”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玩劳动”具有生产性特征,其创造的价值由生产的信息产品等社会认可的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玩劳动”的出现是数字时代休闲“劳动化”和劳动“休闲化”的结果。还有部分学者更强调“玩劳动”的休闲性,提出尽管“玩劳动”生产出数据产品,但是并不一定是以体力与脑力消耗为代价的生产劳动,甚至其生产的目的都不存在。而对这些数据进行收集与处理过程更能体现劳动特征。“玩劳动”的实质是休闲娱乐与社会交往活动,其创造的数据也仅仅是数据工程师劳动的原始材料而已。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的歧见主要聚焦于“‘玩’是一种活动还是一种劳动”以及“‘玩劳动’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吗”。我们认为,厘清问题的关键是要回归马克思关于劳动本质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劳动的本质是人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是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活动。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丰富性和无限发展性,这决定了人用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对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而人类劳动就是在创造一个满足不断发展的人类需要,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属人世界”的过程。因此,理解“玩”是否是劳动的关键在于厘清数字时代背景下“玩劳动”产生的数据产品是否符合人类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同时这种产品是否被纳入社会生产生活体系而具有价值。如果“玩劳动”产生的数据不具有使用价值,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可被交换的具有价值的“社会劳动产品”,更不是商品。产生数据的“玩劳动”也仅仅是一种活动,不能被纳入劳动的范畴。回归马克思主义考察上述问题是解析“‘玩’何以成为劳动”、“何以会有‘玩劳动’”等问题的关键。
二、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玩劳动”的生成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一种新的劳动形态的出现一定是在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作用下产生的。“玩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其形成过程同样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与数字生产方式的形成。其中,数据商品化、数字平台资料化以及经济空间的数字化重构,为“玩”成为劳动奠定了基础。
1.数据产品商品化是“玩”成为劳动的起点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同理,数据商品也是分析“玩劳动”的起点。不可否认,“玩劳动”所产生的数据产品是人造物,是人的体力与脑力生理上的消耗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结果。从个体在娱乐过程中创造的数据产品来看,这些数据是经过“玩劳动”创造完成且可供消费的产品,具有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它的规定也就改变。”用户在互联网平台进行网络购物、浏览网页、消费娱乐、休闲出行等活动产生大量数据,主要表现为一种原料。这些数据原料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经过“玩劳动”的过滤而产生的。这些数据原料的使用价值经过数字劳动者的分析处理,可被用于刻画用户数据肖像、投放定向广告、洞察消费者心理等。从个体在娱乐过程中的生产性行为创造的数据产品来看,随着人们消费需求从对衣食住行等物质性需求的满足,扩大到对精神层面需求的满足,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等在内的数据产品,已经直接成为人们的精神消费品。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商品成为数字经济的细胞,是数字经济新形态下最基本、最抽象的范畴。作为能够生产数据产品的“玩劳动”也就具备了成为劳动的前提条件。
2.数字平台资料化为“玩”成为劳动提供了物质条件
在传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向“产消一体”的“玩劳动”的转变过程中,数字平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的普及和应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迭,数字平台在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的作用下加速渗透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人们从对工业机器的依赖转向对数字平台的依赖。数字平台是可以收集、处理并传输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信息的一般性数字化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脑机接口、移动用户端等各类终端系统,它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首先,数字平台为个体进行“玩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伴随着大数据、Web3.0、5G、数字孪生、扩展现实、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数字平台为“玩工”提供了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以及大部分商品消费、服务、社会交往等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使“玩工”在进行数字活动时,将其所生产出的数据产品进行存储、处理和利用。其次,数字平台作为一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新组织形式,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的上下游结构,为自由个体随时随地进行“玩劳动”提供了渠道。在数字平台中,自由个体在进行消费性活动的同时,可以依托平台共享的数字资源进行生产性的活动,不断地付出产消劳动,无偿为平台资料所有者提供劳动成果。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成为一种新的劳动资料,引发了新一轮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的变革。作为既是进行生产也是消费的工具,数字平台通过赋能更多的自由个体,使其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化为“产消一体”的“玩工”。
3.经济空间的数字化重构将“玩劳动”纳入社会生产生活体系
理解“玩”是否成为一种劳动的核心在于,“玩劳动”如果没有被纳入社会生产生活体系,其产生的数据就不能成为可被交换的“社会劳动产品”,更不是商品。产生数据的“玩劳动”也仅仅是一种活动,不能被纳入劳动的范畴。经济空间的数字化重构把“玩劳动”纳入社会生产生活体系,从而为“玩劳动”从一种休闲活动转换为劳动奠定了社会基础。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不仅极大提高了人们利用、开发、处理信息和数据的能力,还形成了以数字平台为底层架构、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由数字技术驱动的虚拟的数字空间。虚拟数字空间是对现实物理空间的数字化重构和超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时空形态,传统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形式日渐数字化和数据化。从经济现实来看,数字化生产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生产方式。其中,“玩劳动”作为数字空间中的一种劳动形态,也被数字技术所捕获。其次,虚拟数字空间的发展创造出对包括数据、算法、程序、操作系统等数字生产资料的内在需求。一方面,物质生产不再局限于具体实物产品的生产,各种虚拟的数据产品在数字空间的覆盖下也被纳入社会生产体系。另一方面,与传统的生活方式相比,数字时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从现实物理空间延伸至虚拟数字空间,数字化生活成为大数据时代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玩劳动”作为一种现实物理空间中的数字化活动和虚拟数字空间中的数字化生产也被纳入社会生产生活体系。
综上,“玩劳动”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生产方式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劳动形态。“玩劳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具有物质属性和生产性质。与传统的劳动范畴相同,“玩劳动”具有劳动二重性,其具体劳动生产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其抽象劳动生产数据商品的交换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休闲消费的活动都是“玩劳动”,其判别的关键在于这一活动是否创造出具备社会性使用价值和交换性价值的商品,从而纳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环节。如果用户在数字平台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并未纳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环节,则这类活动不属于劳动。此外,“产消合一”是“玩劳动”区别于其他形式劳动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其“特殊性”所在,而这一特殊性其实质是“玩劳动”在虚拟数字空间中数字化重构形成的。
三、“玩劳动”与劳动价值取向的偏离
“玩劳动”作为数字时代劳动与休闲统一的典型具象表达,为个体实现真正自由的劳动提供了可能。然而,当前“玩劳动”与享乐主义、“躺平”主义、消费主义等社会思潮相互交织,且在数字网络建构的空间权利的放大下,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人们的价值理念,对社会正确劳动观的形成造成了负面影响。
1.“玩劳动”与劳动的享乐化倾向
马克思在描述自由劳动时指出,哪怕社会“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尽管“玩劳动”具备休闲的属性,倡导在自由和幸福中达成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仅仅是一种娱乐或消遣。当前,数字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智能机器在各领域的应用将人类从繁重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为实现自由劳动创造了可能。然而,在享乐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部分人错误地把“玩劳动”当成是娱乐和消遣,沉溺于单纯的娱乐享受之中。尤其是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兴起,将人引入休闲异化的陷阱。人的休闲时间被各种娱乐产品、商业广告等所充斥,人在休闲过程中的自我发展需求被物欲所取代,劳动的本质被掩盖,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转变为在物质消费中获取短暂的感官享受。这时,彰显人的主体性和提升人的能力的劳动成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人们满足于虚荣与欲望的无度消费和无法自我节制的娱乐活动,肤浅、浮躁和空虚成为社会的常态。
2.“玩劳动”与劳动的娱乐化倾向
马克思指出:“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玩劳动”可以创造价值,但并不是所有用户在数字平台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都是“玩劳动”。真正的“玩劳动”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是能够创造出具备社会性使用价值的生产劳动。然而,在“玩劳动”与娱乐至上、“躺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容易造成错误理解,认为任何的用户活动都具备劳动属性,从而产生娱乐就能创造财富的错误思想观念。尤其是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空间扩大至数字网络空间以及新一代消费群体的崛起,大众传媒、游戏直播等娱乐行业成为近几年备受关注的热门领域,游戏、直播等行业的人才需求量大幅增加,这使人们的劳动选择出现娱乐化倾向。一些年轻人摒弃“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渴望成为网红、直播,企图通过单纯地享受网络游戏、影视文化、娱乐节目等来创造财富,最终在游戏、娱乐等活动中迷失自我。
3.“玩劳动”与劳动的否定化倾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竞争逻辑和资本增殖逻辑日益渗透和侵蚀社会生产生活,这导致货币和资本在市场化社会中具有无所不能的神力,崇尚资本而否定劳动的观念成为部分人的信仰,劳动及其主体地位不断边缘化。尤其是在当前社会生产力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下,社会精英阶层或资本利益集团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权,尽管“玩劳动”创造具有社会性的使用价值,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玩劳动”的劳动成果却被资本无偿占有。尽管互联网内容创作者、游戏模组爱好者创造了劳动成果,但是在资本的侵袭下却没有获得对其劳动成果的所有权、分配权。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者的“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最终导致为实现休闲和劳动统一的“玩劳动”异化为“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四、赋予“玩劳动”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行动标准
在劳动与休闲相统一的过程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劳动,释放人们劳动创新的潜能,是“玩劳动”在数字时代发展的积极朝向。“玩劳动”的初衷并非是把“玩”当成一种劳动,或是将劳动享乐化、娱乐化、否定化,而是使劳动变成自在自觉的活动,人们既能在劳动中享受乐趣,又能在享受乐趣的同时激发劳动潜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劳动与休闲的统一创造了可能。在当前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为进一步促进人类劳动迈向真正自由劳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根本,发挥新时代劳动精神引领作用,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中引导和规约“玩劳动”,并赋予其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行动标准。
1.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根本,赋予“玩劳动”价值导向
为明确“玩劳动”的价值导向,就必须在全社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对新时代正确认识劳动的主体性、肯定劳动的创造性、树立劳动幸福观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一是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劳动本体论,在社会主义劳动关系中彰显人的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新时代劳动教育中,要让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的生存条件和存在方式,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等科学观念。二是要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论,在社会主义劳动过程中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劳动不仅是塑造、丰富、发展人的根本动力,而且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前提。要改变人民群众将劳动作为单纯谋生手段从而丧失自我价值实现理想的观念,充分认识到幸福必须通过劳动来创造,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历史和未来。三是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与休闲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提高人民群众劳动的幸福感。要改变过去将劳动与休闲对立起来的狭隘的、错误的观念,应该从人类的自由活动、“个人的自我实现”以及“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的角度来理解劳动与休闲的辩证统一关系,激发劳动者的劳动自觉性和劳动积极性。
2.以新时代劳动精神为引领,规约“玩劳动”的行动标准
劳动精神是根植于劳动者内心的价值观念,外化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道德标准、精神状态和行为规范。劳动精神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产生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又包含着对劳动现实的超越。随着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变化发展,加强新时代劳动精神引领,有利于规约“玩劳动”的行动标准,激发劳动者的劳动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为此,一是要科学把握新时代劳动精神的基本内涵。劳动精神是对劳动者的价值引领、情感认同、实践要求以及道德标准的系统体现,“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二是要弘扬劳动精神,形成“劳动至上”的社会新风。要加强社会舆论引导、媒体宣传教育,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实现人生理想,立足劳动岗位成长成才,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摒弃一切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形成弘扬劳动精神的主流意识和社会文化。三是要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引领作用,培养一代又一代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有志青年。要提高劳动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把劳动教育纳入育人的全过程,将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青年正确劳动观形成过程中的引导作用。
3.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 为“玩劳动”的正向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是推动劳动健康发展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超越了资本逻辑,为数字时代劳动者在劳动与休闲辩证统一的过程中,实现真正自由的劳动提供了可能。为此,一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所有制层面明确以社会主义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发展逻辑,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为实现人的自由劳动、激发人们的劳动潜力提供基本制度保障。二是要不断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数字时代人类的劳动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要加快完善符合数字时代经济现实的分配制度体系,尤其是在数字产品确权、数字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维护数字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总之,相比于以资本为内核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超越资本逻辑、引导“玩劳动”朝着劳动与休闲相统一的方向前进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障。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1期,文献略)
推荐阅读
【理论探索】刘振江:马克思“经济社会形态的自然史”论断再探——以黑格尔“精神自然史”为视角
【理论探索】蒋南平 张明明:坚持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 基于马克思劳动及异化劳动理论的分析
【理论探索】王智强 袁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全球化分裂——兼论中美贸易关系
【理论探索】葛扬: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理论探索】张登德:亚当·斯密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形象探析
(编辑:林盼 孙志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