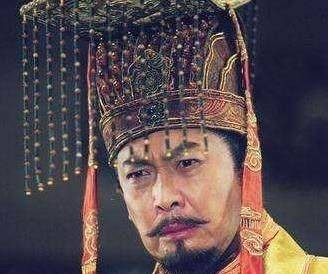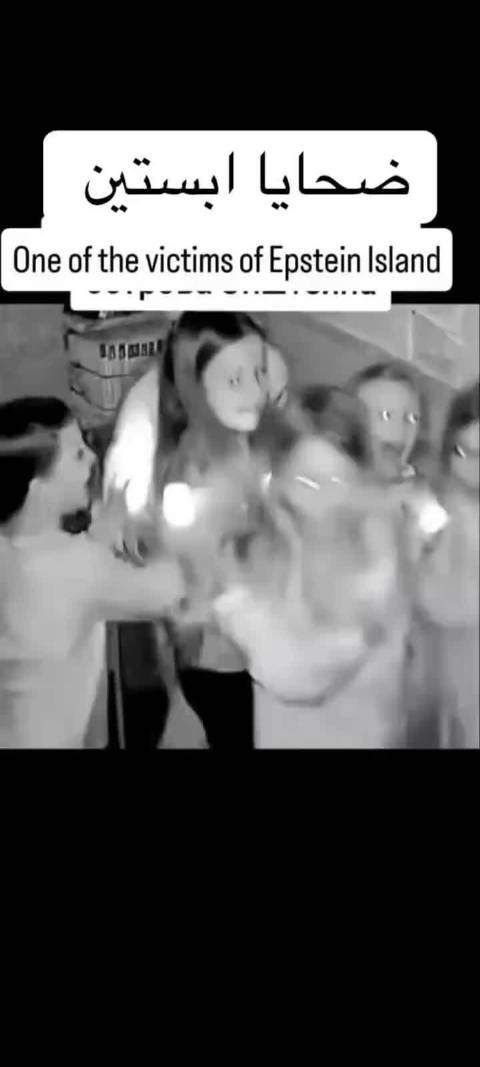在哲学世界中,有一种与人生选择及价值相关的哲学分支,一般被归类为“人生哲学”,对人生困惑的哲学性反思,就是人生哲学的任务。这里所说的人生困惑,究竟指的是哪些问题?比如,我这一生活得有意义吗?在复杂的职场竞争中,我们究竟该如何平衡良心与利益的关系?我们该如何面对代际沟通的种种困难?三观不同,难道真的就只能在微信里拉黑彼此吗?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世界各大学的哲学系却鲜少专门开设人生哲学方面的课程。因为与人生相关的哲学问题其实是被拆成了碎片,散见于不同的哲学板块之中——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欧陆哲学的存在主义等。近期出版的新书《当一切命中注定,我们还要勇敢吗?》,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徐英瑾便从古往今来30位伟大的哲学家入手,试图将散见在哲学史中的人生哲学思想素材加以整理,从而提供给读者一套丰富的“人生工具箱”,而人类的所有困惑,或许在其中都能找到一些回应。
理性至上 VS 在实践中实现理想
先来看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给出的人生哲学提案。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面对的古代雅典社会,虽然在技术的发达程度方面不能与当下相比,但他们面临的基本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却并非完全陌生。
若用今日的流行语去描述古代雅典社会,其社会病症便是,很多人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几乎就被几个“大V”牵着鼻子走。所谓的民意,本质上就是靠刷流量,而不是靠刷智商。当时,“大 V”也就是所谓的智者。智者不是指今天所说的“有智慧的人”,当时,他们更像一群拿了钱,专门帮人洗地的文人。
▲ 拉斐尔画作《雅典学院》中的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与之不同。相反,他们觉得,当时被一群智者操控的雅典民众的道德生活是如此堕落,因此真正的哲学家就需要提出一套系统的理智拯救方案,帮大家走出愚昧,由此摆脱“大 V”的影响。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用真诚的辩论来揭示公共议题自身的理性根据。照此提议,凡是我们在理性上无法接受的事项,便可一概不理。结果,这样的做法反而惹怒了雅典民众。苏格拉底比较倒霉,被愤怒的雅典民众判处了死刑,最后只能喝下毒芹汁,了却自己的一生。而柏拉图曾去过叙拉古(在今天的西西里岛)。他希望能用理性拯救当地人的生活,但也不是很成功。
有人或许觉得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实在太倔强,凡事都要评出一个理来,不碰个头破血流才怪。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决定给他们的理想主义打个折扣,往后退一步。他认为人生的幸福并不仅仅在于能讲理,讲理固然不错,但更高明的境界是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理想。即使实现一半,也比一点都没实现要好。所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你就不得不对现实做一些妥协。亚里士多德认为妥协本身没什么丢人的,关键是要“合乎中道”。在他看来,有德性的人就是做事做人能够合乎分寸之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的人生才会变得幸福。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人生哲学,可以概括为“理想至上”,而亚里士多德的人生哲学就是“求中道”,后者是前者的妥协版本。而有了第一步妥协,就会有第二步,最后一直撤退到古典虚无主义的立场上。
幸福也能被计算吗?
基于实证主义思维的人生哲学,本质上就是基于“理科脑”的人生哲学。很多人或许会误以为一个满脑子理科思维的人是没法过生活的—错了,他们照样在过他们的日子,就是在有些人看来没什么趣味罢了。比如,你和他一起吃大餐,你思考的是如何大快朵颐,而他考虑的则是吃什么会让嘌呤变高,吃什么会让血糖变高,结果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一句话,他们更倾向于在生活中“精打细算”。
有人或许会问 :既然有人说人生的本质是“高三毕业后就迟早奔向‘三高’”,那么在吃饭的时候考虑一下健康有错吗?好吧,基于实证主义的人生哲学可是将这种态度拓展到了饭桌之外。其典型表现便是将计算的态度施加到幸福之上。换言之,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三高”指数是可以被计算的,但基于实证主义的人生哲学家却说 :快乐也是可以被计算的!
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了一套针对快乐的复杂算法,以便社会监管者能够根据这套算法,提高全社会成员的幸福度。这种主张的哲学标签就叫“功利主义”。
根据功利主义,一个行为是否在道德上值得被鼓励,取决于该行为是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给最多数量的社会成员带来快乐。这听上去很有道理,却会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引发争议 :快乐真能被计算吗?一个完全不懂古典音乐的人,能够理解爱乐者的快乐吗?我们能够仅仅因为不懂古典音乐的人要比懂的人更多,而去限制高雅艺术的发展吗?从直觉上看就不对劲吧!
既然快乐似乎很难被客观地计算,就需要被主观地体验。由此引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人生提案。
找寻有存在感的人生
“现象学”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忠实地描述我们能够主观体验到的东西,而不要在悬置体验的前提下,空谈那些基于空洞概念的宏大叙事。“存在主义”的意思是,要在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感,在乎我们与世界的关联是否顺畅。比如,特别要在乎此类现象:单位同事视我为空气,甚至家人也不理解我的抱负与愿景。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我”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从直观体验的角度看,“我”却是缺乏存在感的。
▲ 海德格尔
之所以要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放到一起谈,是因为不少现象学家其实就是存在主义者,而这两种学说在“尊重个人体验”这一方面也有交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有德意志阶段与法兰西阶段。前者的头号哲学英雄是海德格尔,后者的头号哲学英雄是萨特。海德格尔的标志性哲学口号是“向死而生”,而萨特的则是“他人即地狱”。
“向死而生”并不是说不怕死,而是说我们要在不可避免的大限来临时,反思自己余下生命的意义,尽量拓展生命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与那些限制我们人生选择的各种常人的俗见进行斗争,不要人云亦云。
这种主张貌似激励人心,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进行人生选择时,必然会受到伦理规范的限制,而很多此类限制恰恰就来自常人的俗见。换言之,“向死而生”的态度若不被限制,则很容易导致当事人的行为陷入一些道德泥沼。海德格尔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与纳粹主义的一度接近,就是这方面的反面案例。
▲ 萨特
至于萨特,虽然他在哲学上受到海德格尔的不少启发,但是在二战时却坚决站在反法西斯阵营。他的选择不仅与其国籍有关(毕竟他是法国人,而法国一度被德国侵占),也与其哲学思想相关。
萨特的哲学关键词乃是“自由”,而自由则是基于相互承认之上的。你要他人尊重你的自由,你就要首先尊重他人的自由,因此,你也无法将所谓常人的俗见都予以全面悬置。而“他人即地狱”也不是让你视他人为仇寇,而是说他人对你的刻板印象,注定要抹杀你的生命意识的丰富性。意识到这一点的你,不能反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要尽量减少你自己也成为他人之地狱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将会以某种曲折的方式,恢复康德式的人道主义中的某些要素。所以,在他看来,存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尽管这未必是海德格尔的观点。
德式现象学—存在主义与法式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分歧,可不仅仅是海德格尔与萨特这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上帝已死”的大背景下,个体体验的重要性显然上升了,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协调个体与他人关系的社会规范也不能被完全放弃。如何在尊重个人体验的情况下继续做到尊重他人呢?这才是海德格尔—萨特之争的关键所在。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摄图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