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犁的读书生活
家庭幽默日常:爷爷给孙子读错字,全家人笑作一团 #生活乐趣# #日常生活趣事# #日常生活笑话# #家庭幽默日常#
作家孙犁的读书生活
文/邓宾善
孙犁先生是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除了“文革”十年中的一段时间,他无时不与书籍相伴随,读书生活丰富而极有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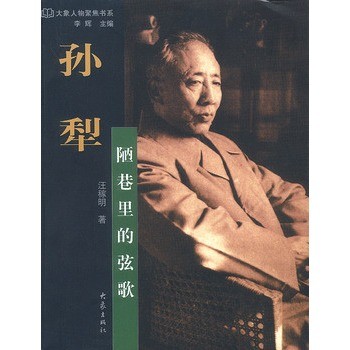
青少年时期的向往读书
孙犁从识字开始,就有逛书摊的爱好。在童年时代,他常常会饶有兴趣地光顾集市或庙会上那些出售小人书的摊位。后在保定上中学的时候,他是附近一个市场里两家小书铺的常客。在大街上也有一些出售“一折八扣”廉价书的摊贩,虽然新旧内容的书都有,但印刷质量大多很差,他路过时也会伫立浏览。老家有一个叫四喜叔的乡亲,知道孙犁爱看书,就把一套《红楼梦》借给他看,使小小年纪的他,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生活的真相。
孙犁高中毕业后,先是在北平流浪,后经父亲多方托人,找到了一个做些抄抄写写的小公务员的工作,但不到一年就又失业了。失业在家的孙犁,想订阅《大公报》,只好硬着头皮向父亲要钱。父亲爱子心切,虽然家中经济上并不宽裕,但还是应允地对儿子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长了可订不起!”
不久,孙犁到家乡镇上的一个小学任教,月薪20元。于是,他开始节衣缩食地函购上海进步书籍,看到《海上述林》的征订广告立即汇款。这是鲁迅先生抱病为亡友瞿秋白出版的著作。孙犁得到邮寄来的《海上述林》,十分珍爱。“七七”事变后,他参加八路军,家人将此书藏之于草屋夹壁,但后被汉奸引敌拆出掠走后不知去向,他听说后伤心不已。

革命战争时期的“野味”读书
走上革命征途后,虽身处战争环境,孙犁却依然不忘读书。战争年代,书籍匮乏,即便爱书如孙犁者,也只能反复阅读他自己所保存的、数量有限的那几本书,或战友间相互交换着阅读,而更多的时候,是碰到什么,就读什么了。每当反扫荡时,他总在一个布包里放上一本书,以便在间隙中,在河滩边,在山路旁,读上几行或几页。他携带的,常常是他最爱读的鲁迅的著作,如《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书。另外,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书,他也是在不同地点断断续续地阅读的。在当时中国农村,有书的人家很少,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很多农家的窗台上,却经常见到几册《聊斋志异》。往往是先在这家发前了前几册,读过了,过了些日子,又在别的村庄读到后面几册。或者遇到的是已经读过的几册,那就再精心地读一遍吧!《聊斋志异》一书,他就是这样错综回环、反反复复,经过了若干年月才全部读完的,其中有些篇章,不知道读了多少次。
解放战争期间,孙犁在河间冀中区党委工作,在大街的尽头,有一片小树林子。每逢赶集的日子,卖废纸破书的小贩,把推着的独轮车,停靠在一棵大柳树下,坐在地上吸烟。纸堆里有些破旧书。有一次,孙犁花很少的钱,从小贩那里买到了两本原版的《孽海花》。他就坐在大树下读了起来,后来回忆时,还感到其味无穷。作家杨朔当时也曾在那里逗留,住在冀中导报社。报社存有一部《全唐诗》,杨朔将它带回宿舍阅读,离开时他并未将书带走。孙犁因对民间艺术有兴趣,因此从这一部《全唐诗》中检出乐府部分,装订成四册,独立成书,取名为《全唐诗乐府》,此诗一直保存至今。他以为,这似乎不能说是窃取,只能说是游击作风,再说那时也没有别人爱好这些老古董。在饶阳县张岗,设有冀中导报社印刷厂,厂长张冠伦是孙犁的熟人,他经常吃住在这个纸厂里。厂里收来的烂纸旧书,就堆放在场院一角的一个大屋子里。孙犁每次到那里,总要蹲在那里刨拣一番。他曾在那里拣到一本石印的《王圣教》(王羲之《圣教序》书法作品)和一本石印的《书谱》。后张冠伦又成了冀中邮局的负责人,他告诉孙犁邮局的仓库里堆放着一些土改时收来的旧书。孙犁专门去翻了一下,找到好几种亚东图书馆印的白话小说,书都是新的,可惜不配套,有的只有上册,有的只有下册。但即使是这些残缺不齐的书,孙犁也极有兴趣,读了很久。
孙犁把上述战争年代类似游击式的阅读,称之为“野味读书”。他后来在以此为题的文章中说:“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阵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可怀念的游击年代!”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活,曾寒酸地买过书:为买一本旧书,少吃一个烩饼,以节省几个铜板。也曾阔气地买过书:面对书架,只看书名,不看价目,随手抽出,交给店员,然后结帐。他得出的结论是:“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他对野味读书,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
孙犁的野味读书,读了许多年代久远的书,孤行苦历的书,以及时代进步的书。他读得十分认真,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下过大量的案头功夫,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于1944年春天,从晋察冀根据地到达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他先后发表了《芦花荡》和《荷花淀》两篇小说,一时轰动延安,好评如潮。他的小说被誉为“诗体小说”,成为引人瞩目的一颗文学之星。如果没有他长达十余年的野味读书,他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开创式成就,是不可想像的。

和平建设时期的沉浸读书
1949年1月,孙犁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此后在天津工作了53年,长期负责《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进城后的读书生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孙犁称之为“广事购求,多方述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
首先,由于所处社会环境和个人意向的变化,孙犁在阅读兴趣和重点上发生了大幅度的转移。导致这种转移的原园之一,是想弥补古文和古代文化知识上的不足,导致他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我的读书生活》)。其次,是阅读环境的影响。初进天津,他见到的是旧货充斥的情景,其中旧书摊也很多,几乎随处可以见到。这使他有机会随时随地接触古旧书籍了,学习古文和古代文化的意愿,也有了实现的可能。
其次,他开始沉潜于古籍的搜求。进城初期,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他只能用节衣缩食省出的钱,遇到什么买什么,阅读时也只能凭一时的兴致,顺其自然罢了。1954年后,他有了一些稿费的收入,可以向正规的古旧书店直接购买或邮购,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购入古旧书籍。他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石印和木版的;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他说:“买书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一样,总是逐步升级,得陇望蜀。”虽然他偶而也有机会出去旅游或疗养,但到了那些有景点城市,只是匆匆地走马看花,他主要关注的,还是当地的古旧书店。因此,旅游和疗养便成了他有选择地购入经、史、子、集等方面古书的一个极佳机会。这固然是出于想当收藏家的考虑,但也是为了自己写作上的需要。他如果不是收藏和阅读过众多的历代杂谈、小说类的笔记,他就不可能写出《谈笔记小说》之类的文章。
与此同时,他还着力于为扶持新人新作的广泛阅读。他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像一个苗圃。他作为一个园丁,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大量新出现的文学作品,连续写出了多篇《读作品记》。他的有关新人新作的评述,言辞恳切,实事求是,视野开阔,发微显幽,年轻作者读了,无不感到获益匪浅,一批文坛新秀由此脱颖而出。
晚年孙犁的读书生活,更是别具一格。他不但依然手不释卷,而且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独创了书皮文字,即“书衣文”。这种写在书皮纸上的文字,记录了他的读书心得、读书札记和他对书籍的珍爱之情。书衣文的写作,从196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5年,前后历时三十一年,写成的书衣文多达550多篇,可见作者用力之巨和用心之深了。
1974年4月,孙犁对书籍的命运感慨良多,不由地提笔书写《书箴》于《西游记》一书的书衣之上:
“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缺,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蠧,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书箴》韵味二则,二十六句,一百零四字,可谓是孙犁的夫子自道。他笔酣墨畅,一唱三叹,既写出了他对书籍的无比钟情,又谆谆告诫世人,对书应抱何种正确的态度,是一篇金针度人、嘉惠后学的绝妙佳作!

孙犁读书生活的当代意义
世转时移,而今已不复是孙犁先生的那个时代,但他当年的读书生活,至今仍不乏借鉴的意义。我们今天的读书生活,至少可从中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启迪。
首先,读书首先要懂得爱书。回顾孙犁一生读书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共识,即他刻苦读书的一腔热情,完全源于他对于书的无比钟爱。这里所说的钟爱,不是指对书的一般性的喜爱,而是指那种对书超乎寻常的痴迷和珍惜,乃至几乎达到了成癖的地步。诚如他所说那样:“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到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觉得是至上的快乐。”(《装书小记》)
其次,一个读书人,必须葆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孙犁读书不盲从,不跟风,不轻信,对所读之书不作特意的选择,更不等别人来推荐。我们也完全应该像孙犁那样,读书的事自己做主,不迷信商业味十足的文化炒作,对各种排行榜也大可不必视作铁板钉钉。读书如游埠,何处只当走马观花,何处却该细细赏玩,完全听凭自己决定,从而进入无牵无挂、澹定从容的读书佳境。
先哲虽逝,遗响犹存。孙犁先生的读书生活,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一种读书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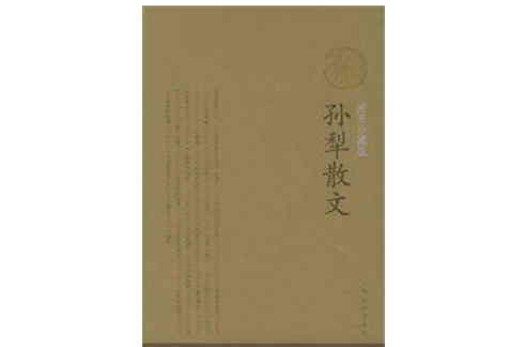
文作者邓宾善,图自网络
(注:您的设备不支持flash)网址:作家孙犁的读书生活 https://klqsh.com/news/view/147974
相关内容
读书生活我的读书生活 作文
秦海璐秒变田秀才,AI爆改犁地小生引热议
读书生活作文
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的读书生活600字作文(汇总16篇)
我的读书生活作文
读书与生活作文800字最新 读书与生活作文高中(精选五篇)
作文:我的读书生活
读书生活的作文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