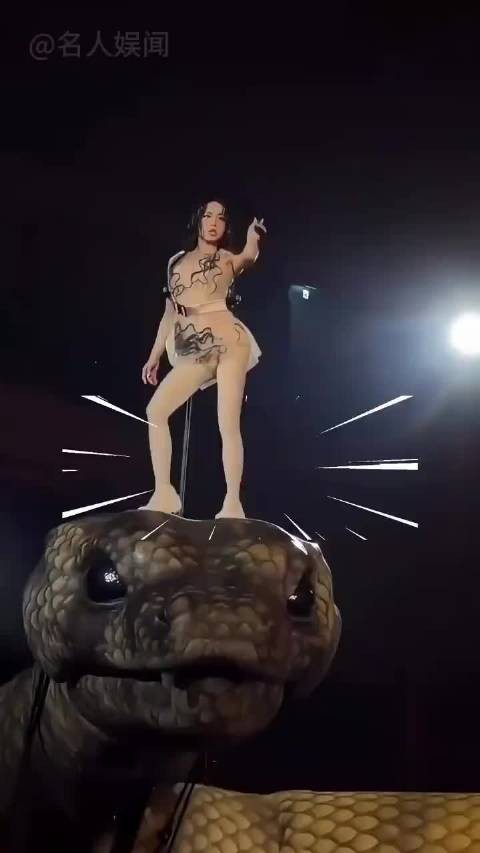李格非
选择背包而非行李箱,轻便出行 #生活知识# #技巧# #旅行出行技巧#
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为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齐鲁著名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证其为人,传其不朽。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官太学录。他专心著述,文名渐显,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同在馆职,俱有文名,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元祐四年(1089年),官大学正[5]。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职期间“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10卷,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富弼)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谢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绍圣四年(1097年),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内排挤元祐旧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党”,被罢官。《宋史·李格非传》:“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党籍罢。”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祐党人(见《宋史·徽宗纪》)。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但禁止到京师及近钱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当时的齐州知州梁彦深游于历山东侧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镌文于“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题名曰:“朝请郎李格非文叔”(乾《历城县志》)李格非卒年不详,《宋史·李格非传》仅载:“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刘克庄评论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后村诗话》续集卷三)。《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南宋楼昉谓其文“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崇古文诀》卷三二)。也能诗,《过临淄》、《试院》等篇清朗雅洁,为人所诵(《后村诗话》续集卷三)。著有诗文四十五卷,今已佚(同上书)。其《洛阳名园记》自宋时即有单刻本行世,今存《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一○三一录其诗九首。《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李格非又为苏轼之门生,李清照之父[6]。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只可惜各书皆佚,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李格非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枫窗小犊》)、《傅尧俞疏》(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墨庄漫录》、《人冷斋夜话》)、《李格非论文章》(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
齐鲁书社出版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家石头上的文献——曲阜碑文录》,第169页可见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经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遂书堂书目》谓有《李格非集》,刘克庄《后村诗话》谓李格非有诗文集四十五卷,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三者可能一书而异名,只可惜各书皆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言其“集不传,馆中亦无有,惟锡山尤氏(文)有之。《皇朝文鉴》仅存此跋(指《书洛阳名园记后》),盖亦未尝见其全集也”。尤氏所藏本,疑即韩淲所说的《济北集》。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称李格非有“诗文四十五卷”,当是《济北集》的卷数。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录《李格非集》四十五卷,盖即据《后村诗话》。李格非文集久佚,《全宋诗》辑其诗九首,零句二,《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其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洛阳名园记》《书洛阳名园记后》《隐士廉复墓碑序》《书战国策后》《幸太学君臣赋诗序》《题韩致尧十一帖》 《左马班范韩之才论》《破墨癖说》《论文章之横》《李格非论文章》《题名》《资忠崇庆禅院劝请大师疏》[7]。
《书洛阳名园记后》
论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肴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8]!
参考译文:
现在我来作一结论:洛阳处于中国的中心,凭藉肴山与渑池的险阻,控制秦川和陇山的要冲,并且充当了赵、魏两地的堡垒,可以说是四方必争之地了。中国若是平安无事还算罢了,一旦发生变乱,洛阳必将首先遭受兵灾。因此我曾经说过:“洛阳的兴盛与衰败,便是中国安定和战乱的预兆啊!”
当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在东都洛阳建馆舍、置宅第的,不下千有余家;等到它发生动乱的时候,接踵而起的是梁、唐、晋、汉、周的残酷战争。洛阳的池塘竹树,遭到兵车的蹂躏践踏,变成了座座废墟;高大的凉亭、轩敞的水榭,也被烟火焚燎,化成堆堆灰烬。它们都与大唐江山同归于尽,没有剩下一处了。因此我曾经说:“这些园林的兴盛与荒废,便是洛阳繁盛与衰败的预兆啊!”
既然中国的安定与战乱,从洛阳的盛衰迹象上可以看出来;而洛阳的盛衰,又可以从这些园林废兴的迹象上看出来,那么我写这本《洛阳名园记》,难道是徒劳无益、白费笔墨吗?
唉,公卿士大夫们正当进用于朝、官高爵显的时候,大都放纵自己的私欲,任意而为,而将天下的治理与荒乱抛在一边。他们想在告老致仕以后安享林园之乐,能够做到吗?有唐一代没落的道路便是前车之鉴啊!
李格非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9]
李格非撰写的《洛阳名园记》10卷,记洛阳名园,自富弼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谢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9]。
妻子:王氏(丞相王珪长女)
王氏(状元王拱辰孙女)[10]
女儿:李清照,号易安居士[11]
儿子:李迒,任敕局删定官
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列传第二百三》[12]
里籍争议
关于李格非的里籍问题,学术界素有争议。
《宋史·卷四四四》和《东都事略·卷一百六十》都说他是济南人。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却据清初诗人田雯《古欢堂集》中的《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一诗得出李清照“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的结论。《山东通志·卷三十四》《疆域志第三·古迹一》亦采用了此说。1956年济南趵突泉的东北侧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郭沫若遂题词曰“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此后,柳絮泉说俨然成为定论,然其中却不无疑窦。王仲闻就曾针对田雯、俞正燮和《山东通志》的历城说提出质疑[13]。
20世纪80年代,山东济南市博物馆于中航根据李清照一生行踪,考察章丘县明水镇西三华里的廉坡村时,发现了李格非所撰的《廉先生序》石刻,指出李格非故乡当在章丘县明水镇。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的《李清照里籍考》亦持此说,认为称李清照为历城人或肯定其出生在历城,都是没有可靠根据的。陈祖美在《李清照评传》中极为详细地考证了明水说。提出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有人对李格非父女里籍为历城的说法有所质疑,并径称其为“章城”人。于中航、陈祖美、诸葛忆兵等均认为后人把原籍章丘的李格非,通称为“济南人”是可以的,此说就其郡府而言是对的。但把他的故居定为历城柳絮泉,却不免有附会的成分[13]。
然而对于“章丘说”,学术界依然存在着疑问。徐北文发表《李清照原籍考》,对《廉先生序》碑文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徐北文认为,即使《廉先生序》碑真实可靠,也不能证明李格非里籍在章丘,他认为李格非应是济南历城人。
邓红梅则在《李清照里籍考证中的新问题―兼与徐北文先生商榷》一文中驳斥了徐北文的说法,认为李格非确是章丘人。侯波的《李清照原籍章丘补证》中亦逐条分析论证,认为“章丘说”真实可信[13]。
而孔凡礼据宋代毕仲游的《西台集·策问》文体原注则提出了另一种研究李格非籍贯的线索:“熙宁中,兖州类试(乡试),中选者解头晁补之、晁端礼、晁端智、晁损之、李昭玘、李格非、李罕”,“传谓格非为济南人,不知何以参加兖州类试。以济南属京东东路,类试应在青州参加。疑格非之祖籍或在兖州及其所属,前人尚未有研究及此者,当考”[13]。
妻子争议
《宋史·李格非传》说李格非“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后来许多人都沿用《宋史》的说法,称李清照之母为王拱辰孙女。王仲闻首次据庄绰《鸡肋编》云“清照之母,为王准(王珪父亲)之孙女,非王拱辰孙女”,“庄绰与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疑庄绰所言为是。”[14]
庄绰在《鸡肋编》卷中的一段记载非常引人注意:“岐国公王珪……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闾丘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皆登科。”对此,王仲闻在《李清照集校注》提出了“以《鸡肋编》与《宋史》较之,后附录的《李清照事迹编年》中似《鸡肋编》仍较可信也”的结论[14]
而据《王珪神道碑》记载:“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卒。”这证明了王仲闻对李清照母亲是王准孙女的推断。1976年3月出土于河南伊川窑底村之王拱辰及其两位夫人墓志铭中薛氏墓志铭进一步证明了此推断的正确性,文曰:“孙女三人,长适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2001年山东省济南市出土的由李格非撰写的《贺仅墓志》之碑,文末署名“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本书籍李格非撰”。这与碑文所刻的李格非曾任左奉议郎完全相符[14]。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中亦采用此说,且在其《对李清照身世的再认识》一文中进一步断定:“王准孙女是他的前妻,前妻早卒后,又娶王拱辰孙女为继室。”[14]
陈祖美又继续推断:李格非在前妻去世后,曾鳏居七八年之久,李清照为其前妻所生,父亲在京师为官,李清照一直寄养在原籍。徐培均、诸葛忆兵亦认同“李格非先娶王准孙女,早卒,再娶王拱辰孙女”的说法,但诸葛忆兵认为“李格非曾鳏居七八年之说没有任何史料证据”[14]。
南宋词人刘克庄: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后村诗话》续集卷三) [15]
南宋学者楼昉:(《洛阳名园记》)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崇古文诀》卷三二) [16]
南宋诗人韩淲:李格非文叔、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号“后四学士”。(《涧泉日记》卷上)
南宋官员尹穑: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
宋代笔记作家张邦基:李格非文叔皆为《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墨庄漫录·卷四》)
北宋文学家释惠洪:格非善论文章。(《冷斋夜话·卷三》)
南宋官员邵博: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其知言哉。(《闻见后录·卷二十四》)
元代脱脱等:①其幼时,俊警异甚。②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宋史》) [12]
影视形象
9词条图册
网址:李格非 https://klqsh.com/news/view/188427
相关内容
李连杰罕见发声,谈徒弟向佐穿衣风格!他的三观还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在李嘉格的人生里,独独没有李嘉格自己”
李子柒获聘非遗推广大使助力非遗传承
登上总台春晚李子柒非遗
原来李嫣的是像他呀,年轻的他长得非常非常的帅…
韩非为国尽忠,李斯悲痛欲绝!
7位非遗老师和李子柒同台亮相
《新还珠格格》四大美女14年后现状,李晟低调赵丽颖耀眼
刚刚发布了重映@李晟Su 主演小燕子版《新还珠格格》动态…
这个李瑾莫非就是原著中那个对女性不感兴趣的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