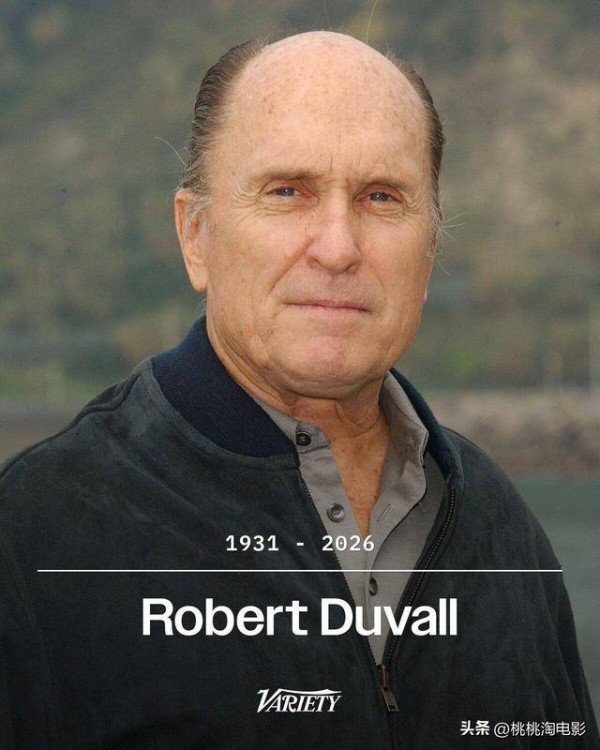01
01
且陶陶,乐尽天真
01
苏轼不是从一开始就成为安贫乐道东坡的,他也曾对人生充满困惑。他在《和子由绳池怀旧》中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1061年所作)
那时他肯定不能料到“雪泥鸿爪”这四字会成为他半生颠沛的注脚——从汴京到黄州,从惠州到儋州,宦海沉浮如雪花消融,留下的只有崎岖路上“蹇驴嘶”的印记。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赏析时说得好,苏轼能熬过困苦,靠的是“对自身状态的幽默感,一点点微笑,他跟弟弟之间的这种相对一笑,这个时刻是永远在这块的。”他会在贬谪中发明“东坡肉”,会在雨夜借竹杖芒鞋吟“一蓑烟雨任平生”,连“骑蹇驴”的窘迫,都以诙谐的方式语尽。可是他不懂的在于,“他对世界充满善意,他无法理解自己何以遭受这样的厄运。”
[元代]赵孟頫《苏东坡小像》,紙本水墨,尺寸不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02
二十余年后,苏轼的好友王巩因为受到使苏轼遭杀身之祸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其歌妓柔奴(寓娘)随行到岭南。后苏轼与王巩会宴,即席创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1083年所作,也有一说1086年)。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是柔奴说的,却在日后成了东坡随遇而安的心法。
03
苏轼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词句“且陶陶,乐尽天真。”其出处是《行香子·述怀》(一说是1086年作)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它已是苏轼生命后期写的词,他看透“浮名浮利,虚苦劳神”,也懂“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的短暂,“虽抱文章,开口谁亲”的孤寂,却偏要在有限的时光里“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天真而非幼稚,是历经沧桑后仍选择对世界报以善意的赤子心,无人可亲却仍愿与溪云作伴的自在游。早些时候,他并没有如此通透,而经过累累岁月,这些,他懂了。
也许“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人生理想,可是“酒斟时、须满十分。”却是真实生活里的常态,很多时候,幸福是通过“不直接的路径”获得的,如果还没获得,那可能另有安排。
《墨竹图》 苏轼
04
又过了几年,苏轼在杭州与好友钱勰小聚,也作饯别。先前,钱勰从都城开封被外放到了越州,而现在,又要从越州调往更偏远的瀛洲。
而苏轼,装着“一肚皮不合时宜”,第二次外调到了杭州。两位天之骄子,在寒门学子看来,早已是高山仰止,景行景止的存在,可是对于斡旋在权利圈层的执政者而言,这二人却是外放的京官,是在党派斗争中步步惊心,前途莫测的棋子。
相见时难别亦难,苏轼写下“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 1091年作)
古人把客舍唤作逆旅,诗文更添了一种逆风而行的背离感,他是宦海浮沉里的“蹇驴客”,是雪泥鸿爪间的“行路人”,被命运推着辗转。彼时钱勰58岁,苏轼55岁。两个年龄加起来一百一十多岁的老人,还如浮萍漂泊,年轻时与兄弟“夜雨对床”的约定,那落叶归根的夙愿,或许这一生都再难实现。
所以这首诗是安慰好友,也是安慰自己,以温情又沧桑的口吻道出了生命真相:
人生只是一个偶然又短暂的存在,固然有很多“高处”和“彼岸”,但生之有涯,跋涉不完无穷的人世间,不妨以一种“旅行者”的身份来看待“生命历程”,不再以期待完美的目的地为方向,用心体会每一段相逢的风景,途中赏遍淡月微云,把离愁化作与好友对饮时会心一笑的温存。“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清朝·项廷纪的《忆云词甲乙丙丁稿甲稿序》
林林总总过后,他已经不论路径何如,只选择顺路而行。贬谪黄州便垦荒种麦,自号“东坡居士”;流放海南便寻芋煮羹,笑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他知如何“把酒当歌”,苦中作乐,从此苏轼作东坡,才成就千年传唱。
《木石图》 苏轼
05
如果说苏轼的乐趣在人间烟火中淘得天真,那华兹华斯的乐趣,就在天际那道彩虹里。借景生情,寓情于物是中外古今诗人的传统。无独有偶,随手翻启的期刊《随笔》里有《华兹华斯的彩虹》,文中载有小诗“目睹天上的彩虹,每次我心都怦怦直跳,我降生世上,它已那般我长大成人,它一如往常跳动”。没有它相伴,我简直无法存活,孩童是成人之父,期盼我能虔敬自然,未来的岁月环环相扣。”亦如此观。
华兹华斯的心跳,充满对生命本真的敬畏——从降生到成年,纵然知道每次看见的彩虹都不是同一道,可正是这“不同中的相同”,让他看清生命的联结:彩虹是地球的永恒现象,而人生如彩虹般短暂,却能在每一次凝视中,与天地对话;他说“孩童是成人之父”,是赞叹孩童对世界的惊奇,把寻常当成“奇迹”:清晨的露珠、傍晚的霞光,甚至石子投入水面的涟漪,都能为之怦然心动。
作家毕淑敏也曾在《保持惊奇》中写道“到自然中去,造化永远给我们以大惊喜。和寥廓的宇宙相比,个人的得失是怎样的微不足道啊。不要小看山水的洗涤,假如真正同天地对一次话,我们定会惊奇自己重新获得活力。保持惊奇,我常常这样对自己说。它是一眼永不干涸的温泉,会有汩汩的对世界的热爱,蒸腾而起,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这不禁让人想起苏轼《赤壁赋》中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两首诗词创作时间相距几百年,思想性却高度一致,用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形容很是贴切:“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应“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诗人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同为杰出诗人,苏轼和华兹华斯在历史追忆与天地宏景中探寻生命真谛的方法至今仍值得仿效。他们都懂,幸福少见光明坦途,而多落于曲折微光处,只有充满对生命的热爱——热爱那短暂却璀璨的彩虹,热爱那漂泊却丰盈的行途,热爱每一个能为月色停驻、为虹影心动的瞬间,发现人间烟火中“常遇常新”的美好,人才可以从经验之河中纵身一跃,投入人生的超验境界,才有可能从生命波荡不平的际遇中超越开来,走向博大。天地常常有大美,永远不用担心前方没有更好的景致。毛姆也曾说:“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一花一草,一事一物,了了于心,探索之心、鲜活之心、余闲之心,皆能护佑我们,这些便是诗人教给我们的乐趣:在人生的雪泥上,以豁达、寻美的态度,做积极有为的创设,留下属于自己的、带着温度的爪印。
附 记
雪泥鸿爪:“飞鸿这么优雅的鸟,它不是在天上飞,它是在雪泥里面践踏,我们每个人都会被人生当中很多沉重的东西,累赘的东西拴在地面上,几乎是一种很悲哀的一种情景。泥上偶然留指爪,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留下一点点的印记,雪是会化掉的,泥也会干掉的,之后就没有任何印记留下来了。雪泥鸿爪,这四个字宿命般地成为苏东坡一生的写照。所以他的兄弟两个人不仅仅是在雪泥上面崎岖地跋涉。没有骑马,他在骑驴,不仅骑驴,而且那个驴还是个赛驴,就从一个优雅的飞鸿变成一个赛驴,就是又有一些幽默在里面。苏轼能够活下来,他很多人生的困苦能够经历,靠着很多是那种他对自身状态的一种幽默感,一点点微笑,他跟弟弟之间的这种相对一笑,这个时刻是永远在这块的。此时,雪泥鸿爪都已从苏东坡的视线里消失,他对世界充满善意,他无法理解自己何以遭受这样的厄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语 出自纪录片《苏东坡》)
推荐书目
《人生得遇苏东坡》
作者:意公子
太白文艺出版社
简介:人生得遇苏东坡,方知可以这样活!
意公子深度解读苏东坡,结合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对苏东坡的人生活法进行层层递进的探究,道出了东坡精神对当下生活的启示意义。
带着“世人为何都爱苏东坡”的疑问,意公子走近苏东坡,历经从惊讶到敬佩再到深识的全过程。她探寻苏东坡的高峰与低谷,研究苏东坡的家庭与感情,分析苏东坡的仕途与交友,在深度共感苏东坡的作品与人生之后,终于了悟苏东坡与命运和解的真正方法。
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面对这个永恒的问题,苏东坡用他的一生给了我们答案。
而通过这本书,我们将和意公子一起,在苏东坡身上照见自己的人生。
本文系属黄浦区公益性文旅项目经费资助项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