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南方写作或诗意小说的新形构——关于龚万莹小说的一点感想
尝试不同的写作形式,如诗歌、散文或小说。 #生活乐趣# #写作#

南方写作或诗意小说的新形构
——关于龚万莹小说的一点感想①
文 · 张清华
谈龚万莹的小说,没有办法不谈到她的地方性,也就是其南方性。因为她一出手,就显示了浓厚的南方情调——更具体一点说,是“闽南情调”。她的叙述中充满了夏日茂密与葳蕤的草木气息,充满了雨季的幽晦与潮湿,还有一种童年时光与经历中特有的缥缈与不确定性。当然,这样说还是让人感到有些抽象,再直接一点说,那便是她的语言的陌生感,那种奇特的“闽南话”的调性。很显然,她的叙述格调与语言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像一位新歌手的出现和被记住,是因为其音色和“声线”的与众不同,其音质的令人惊艳。
显然,当代写作中的“地方性”属性似乎越来越重要了。近年中,先后有了若干区域性的文学现象,“新东北”“新南方”都在争相显现其写作的差异性。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是非常古老的现象。南朝的民歌,类似《西洲曲》《子夜吴歌》那种吴侬软语式的表达,与北方的《木兰辞》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而“文学地理”的差异性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中就已十分明显了,因此地方性的差异性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语言因此而具有不断交融的动力,有在差异中趋同,和在趋同中不断强调地方性差异的变化规律,这样一个古老的矛盾运动。在这一关系中,我们再来观察“南方写作”的重要性,便获得了一个背景和依据。

龚万莹:《岛屿的厝》,中信出版集团,2024
说得再稍微远一点,自东晋以后,中国文学的“轴线”其实就从北方的黄河两岸,南移到了长江流域,南方的文学就得到了迅速的发育。至唐代,诗歌中的风物,其涉及的核心地带早已变成了南方,“春江花月夜”中的景象最为典型,“南方的美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最典范的美学特征。当然,后来中国文学中又出现了第三条轴线,即沿着大运河的轴线,这条线上的景色风物本身是贯通南北的差异性的分布,它们不容易总体化为某一特色,但它因为变成了一条市场意味浓厚的经济命脉,所以在明清之际成为了“小说的主轴”,《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国演义》,再加上集大成者《红楼梦》,它们作者的生活环境,故事的发生场域,基本上都是以大运河作为轴线的。
这当然是一个背景性的粗线条描述,目的是为谈论龚万莹小说的地方性找到一个更广阔的依据。实际上“新文学”的发生,也类似于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北伐”,一批南方背景的知识分子首先在北京创办了一系列新潮文化刊物,如《新潮》《新青年》,无不如此。而“作为文学叙事中的南方”,最典型的样态也是鲁迅小说中的“鲁镇”和“未庄”。南方的风物,南方的人物,南方的腔调,成为新文学最初的正典和已然公认的“正统”。显然,新文学的第一轴线,说到底也是南方。
现在,再来说龚万莹的小说,便获得了一个广远的根基与背景。
这也好像有点离题万里,“从原始社会说起”的意思了。龚万莹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刚刚脱离“文学素人”的身份,我似乎不应设定如此重大的一个话题背景。但有一点无法否认,龚万莹的小说之所以吸引人,让我们无法漠视,就因为她的语言中有非常浓重的南方意味,闽南腔调,还有她叙事中浓密的南方风物的萦绕。这对她来说,也许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却不期应和了我上述提到的古老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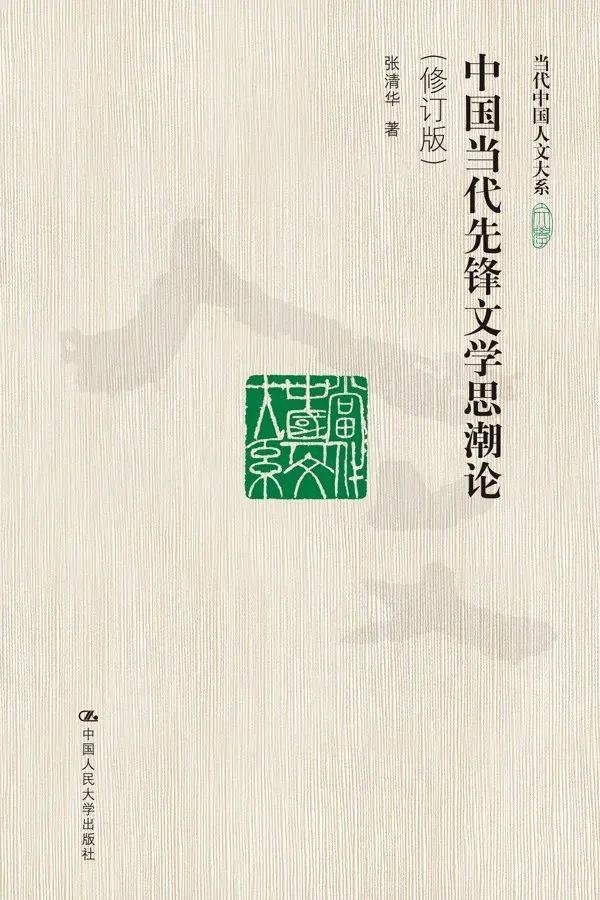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我觉得从经验和感受的意义上,南方的腔调来到北方做一个旅行,即与当年鲁迅的小说一样,会产生出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所谓“地方性”在进入一个更大的语境之后,反而会变成一种“非地方性”,一种更广阔的“超地域性”和“奇怪的时代性”。我们在读到鲁迅小说的时候,不但没有感觉到其南方的属性,反而会感到,这就是应运而出的、最典范的、变革的时代性。当然还有一点,方言本身需要有一种“归化”,即要把南方的语言归化为以“普通话”为主的、以现代汉语的基本特征为规范的、“略带地方性”的一种表述和结构。如果不能完成这种改造,是很难进入公共传播领域的。所以完全用闽南语肯定不行。但是完全用“现成的语言”,其异质性也无从体现。所以,这个“合适的方言载量”究竟需要多少,需要权衡。我认为龚万莹的运用大致是成功的。因为我在阅读中感到“障碍”很多,但新鲜感又恰到好处,并没有感到疲劳和阻滞,这应该就是一种好的效果。还有,我有时会看一下作品中的注释,有时则故意不看,慢慢地就能够“猜”出来。
以《岛屿的厝》为例,“厝”字非常生僻,但它非常古雅且有吸引力。我开始想,她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古老的词,一查方知,它是闽南方言中留下来的古音。古汉语中许多词汇和说法,都是在历代南迁的北方族人的语言中留存下来的,所以这些方言成分反而是“古时的正音”。“厝”字在《诗经》中就有运用,《小雅·鹿鸣》中有“他山之石,可以为厝”的诗句,此为厝的原始用法,为磨刀之意,后引申为安置、房屋(山石状的)等。如此古雅的一个词,在闽南语中居然就是指一座旧式的民居,当然也就是一座孩子眼里的古老而讲究的、有点岁月沧桑的神秘感的老房子。所以它成为一个“意象”,一个在南方的绵绵雨季中坐落的,一个具有古意苍茫的画境的,庇护着童年和承载着时光与记忆的住所……在小说中,也是一个与外婆身份相匹配的甚至互为镜像的象征。而且,它不只构成了这一篇小说的核心意象,同时也成为整部小说集的核心意象。很明显,房子既是一个器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设定,还是一种生命中的怀旧的借喻。
这恰好把龚万莹小说的特点和神韵带出来了,因为它里面确乎充满了怀旧的意绪。而且这怀旧是通过她的童年感受与叙述来实现的。
开篇的《大厝雨暝》就像一首叙事诗,一首有着浓郁的怀旧与伤感意绪的抒情诗。名字也非常诗意,一座风雨如晦中坐落的老房子,在天地苍茫中居伏着的一个老迈居所,仿佛一座有生命的奇怪的伊甸园。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个老人和她年幼的外孙女展开了情感和精神的对话与交往。其中有大量的生活细节场景,刻意琐细的、日常的、显示和标识“慢”的场景,那些成长中的记忆,仿佛是生命中可以任意剪辑组合的梦境。我只能说,这些细节本身或许稍显琐碎和沉闷,但叠加以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一种与童年记忆匹配的“碎片般的迷茫与伤怀”。它们撕开生活的张力很大,叙述的容量很大,几乎装进了家族的历史,只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的那样一个状态,而这恰好就是童年记忆的属性,也是南方雨天刻骨铭心的情景。我不能不说,读它时会出现幻觉,仿佛看见时空深处的幽灵在活动,看到那些生命在依次老去。祖孙两代,一老一小,她们彼此伸出手臂紧紧握在一起,度过漫漫岁月,但又有某种巨大的撕扯力,随时准备将它们扯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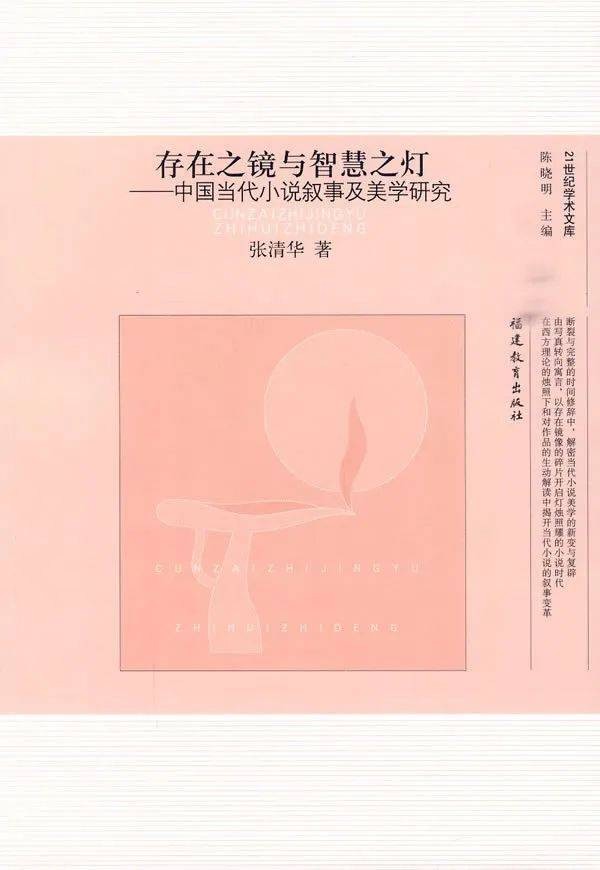
张清华:《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小说的结尾处,是老太太把外孙女带到了墓地。墓地的意象对于孩子来说,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突然出现的“提前到来的死亡”,是哲学情境的降临,感受到“存在”之悟的一刻。那时外公已在墓地里了,日渐苍老的外婆还活在人间,但墓碑上已然刻上了外婆的名字。这深深地刺伤了小鹭禾,她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震撼。这一场景当然也给我们的阅读构成了震撼。最后一句特别像是一首诗的结尾:“阿嬷已经在里面十六年。”这个时空跨度非常之大,刚刚还在眼前,“我”与外祖母还在面对她“未来的归宿”,而转眼间已世事沧桑、物是人非,孙女已经长大,面对的已是墓碑里的阿嬷。这一句一下跨越了至少20年的时光,不禁让人感慨万端。
《大厝雨暝》告诉我们,好的小说不一定是靠故事成立的,这是一篇完全靠诗意成立的小说。
接下来的《浮梦芒果树》,也同样是一首诗,一首苍茫而又感伤的诗。园子中被虫子蛀空咬坏的芒果树再遭砍伐,这是小说的核心意象。但其中妈妈的病作为叙述的暗线,令年幼的孩子隐隐担心,才是事实上的主线。但在处理这一关系时,作者是运用了“遇实虚之,遇虚实之”的置换方式。这篇小说再次证实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小说完全可以像一首诗一样去写,它同样是“以意境胜”。那些树林中的树木都会说话,它们也是岁月中无数拥挤而易损的神灵与生命。它们在风雨中叽叽喳喳,不断用无人听懂的话语交流着,并且多次说起十年后的那场飓风,折断了他们的身躯。小说中这种时间的穿越与错乱感,给人与自然、人与植物之间的混同交集,铺就了合适的背景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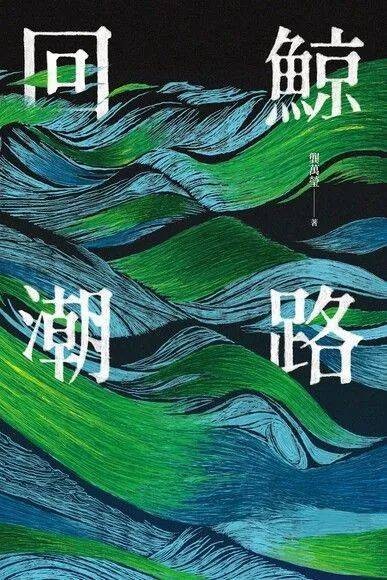
龚万莹:《鯨路回潮》,二十张出版社,2024
还有一点,就是小说中所展现出的新人类的世界观,是令我备感兴趣的。让我无法不感叹,这世界变化太快。在龚万莹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与植物也是平等的,善和恶虽然是分立的,但又不是那样充满血海深仇的对立,因为人性本身是含混交织的,人性中应该充满了悲悯与宽释,包括玉兔的妈妈也是这样,她非常恨她的男人背叛了她,但想想她又放弃了那些恨,并且又回来打理自己的海鲜馆,依然坚强而保有体面地生存下去。书里面的人物都不是以仇恨看待世界和人之间关系的,而都是以爱和宽容。
还有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大厝雨暝》《夜海皇帝鱼》《浮梦芒果树》《浓雾戏台》《出山》诸篇,都给人一种“泛神式”的感觉,因为儿童视角的作用,人与物是如此的贴近,密密匝匝彼此相依互嵌地联系在一起。万物都有灵性,彼此呼应,相融相亲,相爱相杀。我隐隐感觉到龚万莹的精神世界是这样一个充满神性与宗教感的世界。这导致了她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一种哲学和诗学上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还有一点,就是叙述的去时间化、去历史化、无中心化。注意,这个“无中心化”可不是缺点,同时也不是概念化的“女性主义”的属性之类,而是一种新的小说诗学,乃至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充满自我解构的和“叙事中的间离倾向”的新趣味。
这让我想起最近讨论很热的“新南方写作”。我以为所谓“新南方写作”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去中心化。前文中我曾提及,新文学的构造生成与南方方位密切相关,从南方生发的写作观念、人物故事、情感方式、语言风尚,还有鲁迅式的故乡故事所承载的价值观,也同样构成了对于一个传统中心,包括“道统”意义上的主流伦理观与权力观的一种冲击,一种看似颓圮的、民间的、底层的、小人物的、充满喜剧与谐谑气息的叙事形态,恰恰成为新文学的代表和正典,它以轻代重、以逸待劳地颠覆与瓦解了传统文学的那些规制与正统,以地方性确立了时代性。正是这种力量的释放,才构成了新文学生机勃勃的多元局面。这就像现代性、革命与现代中国的经济结构一样,也是由南及北,它既是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是空间的进程,从南方向北方传导和弥漫。在文学上,所谓的“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我以为其精神要义,不是强调地方性中的“文学地理属性”,而是在于一种新的变革诉求,以及这种变革的“曲线运动”方式。
龚万莹的写法和传统的“戏剧性与故事化”的写法很不一样,这在艺术上也构成了去中心化的特点。即她是以意象作为小说的本位的。如果给她归纳或命名一个小说类型的话,她可以称作“意象型的写作”。这种写法最初在先锋派作家那里,尤其在苏童早期的小说里是非常突出的。而现在,这一写法在龚万莹的小说中获得了新的延伸。通过意象的不断叠加式的晕染,生成了一种绵密而浓郁的诗意。这诗意是裹挟着大量地方性文化气息的、有着南方气味的,虽然尚有含混之处,却也带着强烈的可阐释性的一种特征。她用这样一种充满新鲜感的叙事,给当下写作的某种滞胀和沉闷的现场贡献了一种新质,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点清新的气息,一缕新鲜空气的注入。假如要我说出龚万莹小说有什么独特的意义的话,也许刚好应和了“南方写作”的话题。只是在我看来,“南方写作”或“新南方写作”,并不仅仅限于当下的文学时空,而是一个更为久远和恒常的规律。◇◆
◆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 释:
①该文中所引作品皆出自龚万莹《岛屿的厝》(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
网址:张清华|南方写作或诗意小说的新形构——关于龚万莹小说的一点感想 https://klqsh.com/news/view/11710
相关内容
李贺17岁写的神作,韩愈惊为天人,王安石说句大实话却被批不懂诗李清照埋怨丈夫“无能”写诗讽刺,内容大胆,没成想此诗流传至今
小说《国宝》:回顾故宫文物南迁之路,以民间立场看近代中国
原创怪才诗人大雪纷飞中写此诗,从开篇惊艳到结尾,当真是高手在民间
苏轼苏辙重逢共赏月,苏轼写一首《阳关曲》,杨万里评:四句皆好
辛弃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金钱与数不清的姑娘
瑕不掩瑜:说说《金瓶梅》里的写作硬伤
红楼梦里最不会写诗的两个人,却写了两句最好的诗
“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北京,有一群吟诵古诗词、传承“叶调”的人
《楚诗予贺知庭》小说:情人节这天,是楚诗予儿子的生日

